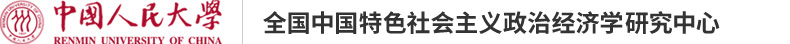刘元春:疫情长期化下宏观经济政策的再定位
发布时间:2020-07-24
目前学术界对疫情的判断已经发生了一些新变化,形成了一些新共识。这些新变化和新共识决定了世界抗疫进程、经济复苏模式以及相应的政策都必须做出相应的调整。疫情的新变化和新规律决定了未来宏观经济政策的再定位。
根据SCIENCE和其他几个学术平台发表的近期文章,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几个新共识:
第一,新冠病毒可以在一年内任何时候扩散,没有固定时间。
第二,感染者治愈后很可能无法获得长期的免疫力,之前某些国家或地区提出的群体免疫可能并不会取得好的效果。
第三,新冠病毒的突变率非常高,对环境的适应力很强,这种情况可能会影响疫苗效果,导致研制的疫苗在短期内有效,而在未来不一定有效。
第四,无症状病毒携带者和一些新发现的情况证明我们对病毒的传播路径和方式依然不是十分清楚。最近几位科学家指出病毒早已存在,只是现在被激活而已。
第五,疫苗与特效药的研制时间比想象中要漫长,且充满不确定性。
第六,病毒很可能将与人类长期共存,疫情很可能持续存在并反复出现。
这些变化和共识直接导致许多研究团队在进行宏观分析中考虑的不仅是二次冲击和二次暴发的问题,而是多次反复暴发的问题。这种情况会导致目前的政策应对会出现一些变化。
疫情持续的时间拉长和影响的范围拉宽将会引发一系列重大问题:
第一,疫情并未像预期中那样在6至7月份到达顶点,疫情拐点的出现大大延迟。特别是进入7月以来,以欧美为主体的世界疫情第二板块蔓延还在持续上扬,以拉美、南亚和非洲为主体的第三板块蔓延已经抬头,同时北京、东京以及首尔已取得疫情阻击战阶段性胜利却都出现了疫情复发,世界确证病例超过1300万,日增超过17万,让未来疫情的可控性增加了非常大的变数。
第二,随着防疫周期不断延长,防控成本也在加速提升。
第三,发达国家前期布局的疫情防控方案和救助方案可能会失效。例如,欧美之前提出的群体性免疫理论框架可能会崩溃;欧美所设计的第一轮疫情救助方案难以承受疫情时间的持续,安排的经费可能很快会用光,政策工具可能消耗殆尽。
第四,疫情带来的混乱状态很可能造成超级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的全面爆发,社会隔离、生活方式的调整可能会带来社会情绪和秩序的超级变异。当前世界经济存在“日本化”倾向,即长期停滞的经济状态可能更加低迷,这可能会使我们原来所面临的结构性问题更加突出。使一些社会冲突、政治危机全面爆发。例如当前美国爆发的BLM运动,巴西和印度以及一些非洲国家所发生的骚乱。从历史经验来看,社会冲突和政治危机等国内问题可能会带来国际问题的全面恶化。疫情的长期化将成为一个超级催化剂,使我们原来就面临的问题变得更加严峻。
对于中国而言,疫情长期化带来的冲击可能会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世界经济触底的时间推迟,并非以前预期的第二季度。在外需下滑冲击延后的情况下,疫情对经济的冲击可能会在第三季度到达高点,并且第四季度依然存在。所以未来的不确定性是非常大的。
第二,世界疫情带来的第三波冲击与第一波和第二波带来的冲击将具有很大的区别。第一波、第二波冲击主要是对供应链的冲击,但是第三波冲击更多是针对需求侧。
第三,欧美第一轮救助政策耗尽,下半年可能会出现几个超级调整。今年上半年出现了五大史诗级变化,下半年经济相应的变化也会十分剧烈。第一,经济处于底部的时间比想象中要漫长,导致政府补贴耗尽、企业破产加剧;第二,金融持续加码,脱实向虚现象更为严重,世界金融市场出现第二次剧烈调整是大概率事件;第三,美元指数可能出现大幅度的调整,美国货币体系和国际金融市场将出现混乱,人民币的铆钉效应强化,资本流入中国的现象加剧。
第四,经济危机与社会危机导致美国出现政治危机,这种政治危机很可能被美国大选激化,从而导致中美冲突达到新高度。这种政治风险外溢将会导致中国面临的经济风险加剧。全球金融资产定价不单是由自身收益率决定,社会风险、政治风险会导致金融定价规律发生超级变异。
第五,国内疫情的反复将给国内经济主体带来的冲击,会导致预期模式、工作和学习方式发生巨大变化。
第六,疫情反复导致经济局部出现二次停摆。
第七,疫情常态化与短期救助之间存在冲突。在第二季度特别是6月份以来,我国计划从短期救助向中期复苏的节奏全面迈进,然而疫情的二次暴发会使中期复苏的一揽子规模性政策的节奏被全面打乱。
针对以上状况,我们可以从以下七个方面采取应对政策:
第一,宏观目标调整应该从短期年度目标向中期目标转变,特别是以疫情周期为统筹对象进行目标设定和工具选择。
第二,由于疫情防控转向中长期化,政策空间要有新的规划。现在很多观点认为我国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空间很大,所以前期的力度可以更大。但是目前我国的财政实际赤字率在今年可能会达到11%,并受到汇率因素、中小银行风险、呆坏账延期的影响,货币政策的空间也十分有限。因此,政策不能够一次性全部投入,要为明年留有余地,甚至要为后年的一些变化做好充分的准备。
第三,扩大“六保”与底线管理的内涵。底线管理的内涵必须扩大,金融风险、政治社会风险的外溢效应对经济领域的影响比想象中要大,要将风险管控重新提上我们的重要议程。特别是全球经济变异给中国资本市场带来的变化,以及中美贸易冲突、大国博弈中的政治风险对经济领域的冲击需要研究得更加清楚。通过最近几个爆雷事件以及中小企业潜在的问题,我们会发现利用中小银行进行针对中小企业的救助,其带来的风险可能比问题本身要大,这一问题十分棘手。
第四,双循环战略可能还要进一步深化,特别是要提高对国际货币循环的重视,在国际货币体系重构以及金融战应对上要有更深入的思考,而不是简单的从实体经济、内贸与外贸一体化和互相促进的角度来考虑问题。国际金融的循环、国际货币体系的循环都非常重要。
第五,要进一步推进新动能的构建,使之与后疫情社会政治运行体系调整有很好的衔接和匹配。要将“非接触经济”的打造上升到战略层面。要考虑一揽子政策里以新基建为主体的政策是否能够担任我国新经济模式加速转型的重任。
第六,要推进一次性短期行政救助体系与制度性、体制性救助体系的构建。任何一个制度性救助体系构建得很好的社会,在这次疫情中的表现都十分良好。如果疫情中长期化,这就要求我们在制度性的保障和救助上面要有所突破,特别是在收入分配体系的大改革上面要有所突破。
第七,把握好缓慢复苏与快速复苏的节奏。要思考如果疫情防控中长期化,快速复苏的节奏应该把握在什么水平。同时,我们提出的需求侧提升和供给侧结构性调整到底如何相互配合?都需要我们做一些深入思考。疫情常态化并不是一句空话,我们要在各种政策里面优先考虑疫情防控,所以疫情扩散基础性的预测就显得尤其重要。
文章来源于中国宏观经济论坛
作者:刘元春,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中国人民大学全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执行主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