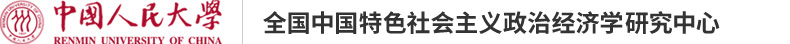刘守英:农民入城还是回村决定着现代化方向
发布时间:2024-06-11内容摘要:中国城乡关系在2003-2010年间发生了革命性的跃迁,告别了那个以农为本、以地为生、以村而治、根植于土的“乡土中国”,进入乡土变故土、告别过密化农业、乡村变故乡、城乡互动的“城乡中国”阶段。与已经走过的城市化上半场相比,下半场最显著的变化是进城农民的代际差异。针对这一差异,我们应给予政策支持,解决农民进城后的问题,让他们在城市中安定下来。这样才能促进中国的转型和现代化。
历经近百年的结构变迁,中国城乡关系在2003-2010年间发生了革命性的跃迁,告别了那个以农为本、以地为生、以村而治、根植于土的“乡土中国”,进入乡土变故土、告别过密化农业、乡村变故乡、城乡互动的“城乡中国”阶段。
这一变革的根源在于农民与土地、农民与村庄关系的根本性变化。而推动这一变革的主力军,正是农二代——这批继承了上一代离土、出村传统的农民,他们中的大多数选择了不回村、不返农的道路。这一选择导致了人地关系、农地制度、农业经营制度、农业发展方式以及村庄的演化与分化等方面的重大变革。
改革开放以来,农民的离土出村成为推动中国从乡土中国向城乡中国转型的最主要力量之一。自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迁移的“农一代”,在经历了多年的城市漂泊和艰苦打拼后,往往选择“返乡”和“回村”。“农一代”很少有长期留在城市的期望,他们通常忍受更长的工作时间和相对艰苦的居住条件等,以便在尽可能短的时间积累更多的资金,攒足回家过日子的费用。
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快速推进,为农民入城创造了机会。但是,中国农民撞城入城后,城市的权利依然只赋予本地市民,为经济社会发展做出巨大贡献的农民工群体没有享受到与城镇居民同等的基本权利和公共服务。
2010年前后,中国的城乡关系发生革命性跃迁。在城乡人口迁移中,80、90后已经成为主力军。他们在经济社会等方面的行为特征呈现显著的代际分别,甚至具有不可逆性,成为引领中国城乡关系变革的重要力量。
他们保留着农民身份,但已不再务农。农二代差不多进入劳动年龄就开始离开家乡,他们的初次外出务工平均年龄为21.7岁,与农业和土地的关系疏离,每年平均在外时间达9个月,不像他们的上一辈那样农忙时回家打理农事,他们之中87.3%的没有从事过任何农业生产劳动,平均每年花费在农业活动的时间仅0.7个月。
他们的受教育程度更高,平均受教育年限达到9.515年。他们迁移的距离离家乡更远,跨省流动、前往东部地区以及大中城市务工经商是他们的主要选择。
他们既看重在外挣钱,也更加注重家庭生活的完整性和孩子的教育成长。他们中有很大比例的家庭将孩子带在身边,在流入地接受教育到初中程度,高中期间由父母一方回县城陪读,直到孩子完成高考。
他们的生活方式基本城市化,农二代在城市的消费方式已经与城市同龄人趋同,乐于通过商场、公园等城市公共设施从事休闲娱乐活动,在外面挣得的收入70%在城市消费。
他们融入城市的意愿很强,农二代在工作地社保享有比例显著高于农一代,但是由于城乡之间的那堵墙的隔离,他们对不被城市接纳的感受更强。农二代的“出村不回村”,正在令乡土变“故土”,传统乡土社会的人际关系、礼治秩序、非正式规则等正面临严重冲击与挑战。
离土出村不回村的一代人,他们的经济和社会行为变化,正在引发乡村经历一场历史转型,标志着一个与“乡土中国”不同的“城乡中国”的到来。如果有一天他们还要被迫回到自己的村庄,那将是中国转型的失败。
农二代面临的严峻现实是,他们如果不回村,进城就成为主要的选择。他们的未来,将取决于城市权利向农二代的开放。与已经走过的城市化上半场相比,下半场最显著的变化是进城农民的代际差异。若继续沿用对待农一代的公共政策来应对这一革命性变化,将给中国转型带来巨大挫折。
我们必须要考虑中国农民的未来。长期以来我们在农民问题上,一直没有一个让农民成为城里人的制度设计。自20世纪50年代起,户籍制度将农民与城市人划为两类,限制了农民的流动与发展。尽管后来乡镇企业发展,农民可以在家乡从事工业,但他们仍被束缚在土地上,身份未变。再到后来,即便进城,也缺乏落户政策,使他们成为城市的漂泊者。
政策设计一直基于农民会回乡、应该回乡的假设,但这样的思维只会让农民永远停留在原地。农民的现代化必须通过他们从乡村到城市的转变来实现,这是现代化的基本形态。如果我们的政策不能促进这种转变,那么现代化就无从谈起。
目前,两三亿人漂泊在外,漂不动了又回到乡村。一个国家如果大部分人口仍是农民,且无法被城市接纳,无法在城市化进程中实现转变,包括他的精神生活、文明形态、观念,创造财富的能力等,不能成为城市中平等的一员,那么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将受到严重阻碍。因为没有一个国家的现代化是通过让农民留在乡村来实现的。
解决农民进城后的问题,关键在于让他们在城市中安定下来。农三代,那些在城市中出生、成长的孩子,他们对城乡间的不平等已不敏感,但制度上他们仍被区别对待。我们需要从教育平权开始,为他们提供平等的受教育机会,因为这是他们在城市立足的基础。
当农二代获得居住权,农三代获得教育权,他们的家庭便能在城市中稳定下来。有了这两个“稳住”,农民是否回乡或留在城市,便成为他们的自主选择。我们应做的,是确保农三代享有教育权,农二代享有居住权,这样农民在城市中的生活才能更加体面。
农民的去向,取决于我们对待农民的基本理念,“十四五”期间是农民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窗口,农民现代化取决于对农民入城还是回村的政策选择,这些政策选择决定了中国现代化的发展方向。
面对乡村老人日益严峻的生存现状,传统的养儿防老模式在现代化的冲击下已难以为继。我们亟需深入剖析乡村老人的生活状况,重塑其生活境遇,提升生活质量,为乡村老人点燃希望。为此,我们必须进一步提高养老保障水平,改变乡村养老保险“广覆盖、低水平”的现状,逐步缩小城乡养老保障体系的差距。
同时,必须摒弃将老年人视为负担的陈旧观念,在乡村经济活动主体长期是老年人的现实下,积极开发乡村留守老人的人力资源。通过推动他们参与农业技术服务项目、社区服务,建立老年人协会等社会组织,让他们的晚年生活更加充实、有意义。
作者:刘守英,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教授
本文转载自公众号乡村发现。文章经授权发布,如需转载,请统一注明出处人大政治经济学论坛及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