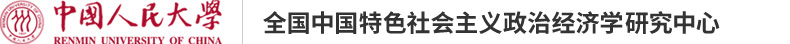齐昊等:国外学者论资本
发布时间:2022-10-26内容摘要:本文从资本与新技术、资本形态与结构、资本对分配的影响、资本垄断及无序扩张四个角度梳理了近年来国外学者针对资本问题的16篇研究成果。首先,本文概括了资本与技术创新间的相互作用。除新技术外,金融化、全球化、无形资产、国家与资本的关系的发展也为资本形态与结构带来新的变化。之后,文章梳理了国外学者对当代资本主义国家国内、国际分配不平等的成因研究。最后,本文总结了资本垄断与无序扩张带来的严重后果。
资本历来是国外学者关注的热点问题。近年来,国外学者主要从资本与新技术、资本形态与结构、资本对分配的影响、资本垄断及无序扩张等方面研究资本问题。
一、关于资本与新技术
资本为新技术的研发与应用提供资金和商业模式,有力地推动了新技术的发展,而新技术所带来的潜在收益反过来也给资本带来了巨大激励,引发了资本的寻租与投机行为。
劳尔·德尔加多·怀斯、马特奥·克罗萨·尼尔:《资本、科学与技术:当代资本主义的生产力发展》(Raúl Delgado Wise and Mateo Crossa Niell, “Capital, Science, Technology: The Development of Productive Forces in Contemporary Capitalism”, Monthly Review, Vol.72, No.2, 2021)
本文以马克思提出的“一般智力”概念为出发点,对当代垄断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生产力组织方式进行了讨论。在马克思那里,一般智力是指一种由积累的知识和技术所创造的集体性、社会性智力。在生产力加速发展的过程中,一般智力采取了越来越复杂的模式。以硅谷帝国创新系统为例,作为全球创新结构的一个支点,硅谷在一般智力的组织架构下控制了不同国家大量智力工作者的科学和技术劳动,创造了一种新的、极端的不平等交换方式。通过这种交换方式,参与科技创新的高技能劳动力的形成和再生产成本从中心国家转移到外围和新兴国家。同时,垄断资本可以通过专利和司法制度获得垄断性的技术租金。本文认为,在当今时代,垄断资本不再是生产力发展中的一个进步因素,而是一个寄生实体,它本质上具有食利和投机功能。垄断资本的背后是一个有利于私人占有和一般智力产品集中的制度框架。
马修·蒙塔尔班、文森特·弗里甘特、伯纳德·朱利安:《作为资本主义新形式的平台经济:调节学派的视角》(Matthieu Montalban, Vincent Frigant, and Bernard Jullien, “Platform Economy as a New Form of Capitalism: A Regulationist Research Programme”, Cambridge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43, No.4, 2019)
随着优步等数字平台的发展,“平台经济”的概念得到日益普遍的应用。这种新的经济形式正在促使资本主义发生转变,而这种经济形式的本质是什么仍然不得而知。本文采用法国调节学派的方法,刻画了平台经济内在竞争形式的本质与转变。本文认为,平台经济的兴起内生于金融化了的积累体制,是这一积累体制出现危机的结果。本文发现:第一,从货币和金融体制来看,平台经济具有“赢者通吃”的特点,因此在平台发展前期需要大量来自风险资本的资金。平台的发展战略就是吸引足够多的用户,获得垄断地位,进而上市变现,而风险资本的目标就是寻找新的“独角兽”。第二,从竞争形式来看,平台的出现威胁到了传统企业。平台相对于传统企业有一系列的优势:信息技术的发展使外包变得更加容易;平台具有网络效应,规模越大成本越低;平台更容易雇佣低工资国家的工人;平台动员了用户,使用户为平台提供互补性服务;平台可以动员用户所拥有的闲置资源,而闲置资源的租用以拍卖方式定价,能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价格。第三,从劳资关系来看,平台经济的典型特征是劳动的“优步化”,这是劳动弹性化和个人化的进一步发展。平台经济雇用了大量自由职业者,特别是低技能的自由职业者,以此把风险和成本转嫁到没有制度保护的劳动者身上。第四,从国家干预来看,平台经济的兴起意味着国家公共政策的“硅谷化”。所谓“硅谷化”就是硅谷的文化和意识形态侵入到政治领域。硅谷的企业家们推动政府用他们的数字化办法解决传统的公共问题,而又不想让官僚体制对其施加任何监管。
综上所述,一方面,在资本的支持下,数字经济和平台经济利用信息技术显著地提升了经济的运行效率。同时,资本构建了庞大的全球化创新体系,整合了各国智力工作者的创新活动。但另一方面,少数大资本在推动创新及新技术开发与应用的同时,通过控制创新、逃避监管、干预政策制定等手段加强了垄断,并以此获取巨额收益。
二、关于资本形态与结构的新变化
国外学者主要从金融化、全球化、无形资产、国家与资本的关系等方面揭示资本形态与结构的新变化。
迈克尔·赫德森:《金融资本主义与工业资本主义:食利者的复兴与接管》(Michael Hudson, “Finance Capitalism versus Industrial Capitalism: The Rentier Resurgence and Takeover”, Review of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ics, Vol.53, No.4, 2021)
马克思及其同时代的许多人都认为,工业资本主义的历史作用是清除封建主义的遗产,使地主、银行家和垄断者无法在不生产实际价值的情况下攫取经济租金。然而,工业资本主义的这一功能在今天越来越无法发挥作用了。在当代资本主义条件下,金融、保险和房地产部门重新控制了政府,创造了新的租金经济。本文认为,这种后工业金融资本主义的目的与19世纪经济学家所了解的工业资本主义相反:后工业金融资本主义主要通过攫取经济租金而不是通过积累工业资本来寻求财富。今天的世界正在被一场关于它将拥有什么样的经济体系的经济战争所分裂。工业资本主义正在输掉这场斗争,而金融资本主义已经成为工业资本主义的对立面,正如工业资本主义在历史上成为后封建地主制度和掠夺性银行的对立面一样。
考斯达斯·拉帕维查斯、伊万·门迪塔·穆诺兹:《美国金融化的分水岭》(Costas Lapavitsas and Ivan Mendieta-Mñoz, “Financialization at a Watershed in the USA”, Competition & Change, Vol.22, No.5, 2018)
本文指出,在2007-2009年大衰退之后的一段时间里,美国经济的金融化达到一个分水岭,其特点是金融利润增长停滞,金融部门和抵押贷款债务比例下降,公共债务比例上升。第一,金融利润自危机以来没有完全恢复。在过去10年中,美国银行的盈利能力持续受到压力。第二,抵押贷款债务相对于个人可支配收入的比例自1980年代以来首次大幅下降,这一发展对金融体系具有潜在的重大影响。第三,美国政府向金融机构提供了大量支持,将名义利率降至零附近,并实施非常规的政策措施,同时向银行提供充足的流动性。其结果是国家债务大幅增加,基本抵消了家庭债务的下降。此外,通过对美国金融化主要宏观经济指标的分析,本文提出这种结构性的突破可以追溯到大衰退时期。自1980年代初以来,美国家庭对正规金融体系的依赖首次出现了减弱。当然,这并不意味着美国金融体系不再容易出现泡沫和不稳定,美国经济仍然处于复杂的金融化状态,而政府提供的流动性推动了金融资产价格的上涨。本文认为,自大衰退以来,美国的金融化程度相对减弱。其未来的金融化道路可能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在国债和金融监管方面的政策。
特里斯坦·奥弗雷、乔尔·拉比诺维奇:《金融化与离岸外包的联系和美国非金融企业的资本积累》(Tristan Auvray and Joel Rabinovich, “The Financialisation-offshoring Nexus and the Capital Accumulation of US Non-financial Firms”, Cambridge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43, No.5, 2019)
本文从金融化和全球化相关联的视角讨论了非金融企业的金融化问题。自1980年代以来,总投资水平下降和利润率高企一直是发达国家的一个典型趋势。这一现象在宏观层面上被解释为非投资的有效需求使利润得以实现,而在微观层面上则通常被认为是股东价值导向的结果。然而,这些解释忽略了一个问题,即考虑到当今的企业资本积累是其未来盈利的前提条件,现有的低投资—高回报战略如何具有可持续性?本文认为,在过去几年中,使这种战略得以持续的条件之一是生产的离岸化。具体而言,金融化和离岸外包具有相关关系,两者都是非金融企业投资减少的决定因素,且金融化主要发生在容易进行离岸外包的行业当中。本文对行业数据的分析发现,金融化及其与离岸外包的相互作用主要体现在大型企业中;金融收益与资本投资之间的负相关关系主要存在于高离岸化行业的企业中,而低离岸行业的企业投资与其金融收益之间没有明显的相关性。以上结果表明,企业更可能将非核心活动外包给外国企业,而核心活动更可能在国内进行生产转移。对那些以资本积累为代价进行金融收益分配的企业来说,分配给股东的收益实际上来源于全球价值链。
厄兹居尔·奥尔汉甘兹:《无形资产在解释投资—利润之谜中的作用》(Özgür Orhangazi, “The Role of Intangible Assets in Explaining the Investment–Profit Puzzle”, Cambridge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43, No.5, 2019)
新世纪以来,尤其是2008年全球性金融危机以来,美国非金融企业的利润率较高,但资本积累率放缓,这说明投资与利润之间的关系出现弱化。现有的研究大多将金融化和全球化作为资本积累率放缓的原因,而本文则提供了另一种解释。本文认为,在金融化和全球化之外,我们还应该注意到过去20年间非金融企业使用了越来越多的无形资产。品牌、商标、专利和版权等无形资产对投资和利润之间的不对称关系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其原因是:无形资产的使用使企业增强了市场势力和盈利能力,同时不必相应增加固定资本投资。本文讨论了非金融企业使用无形资产的不同方式,并在美国大型企业的经验数据中发现:第一,无形资产与资本存量之比普遍提高;第二,在无形资产占比更高的行业中,投资与利润之比更低,成本加成率和利润率更高;第三,非金融企业部门的构成发生了变化,高科技和医疗行业的企业占比出现增长,但这一变化并未体现在投资份额之中。总体上,无形资产较少的企业,成本加成率更平稳,投资与利润之比更高;无形资产密集的行业,其利润率比其投资份额或资产份额增长更快。
米兰·巴比奇、哈维尔·加西亚-贝尔纳多、埃尔克·M.海姆斯克:《跨国资本的兴起:21世纪的国家引导型外国投资》(Milan Babic, Javier Garcia-Bernardo, and Eelke M. Heemskerk, “The Rise of Transnational State Capital: State-led Foreign Investment in the 21st Century”,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Vol.27, No.3, 2020)
本文认为,由国家引导的跨国投资增多是近年来兴起的一个全球政治经济现象。这些跨国投资在21世纪的资本主义世界挑战了有关主权与国家权力的传统观点。本文发现,不同国家在对外投资时采取了不同的战略。一些国家寻求扩大投资回报,从而采取了金融性投资战略;而另一些国家在对外投资中采取了控制性投资战略。国家主义经济体在国家引导的跨国投资中更倾向于采取控制性战略,而自由主义经济体则采取了金融性投资战略。需要强调的是,这两种战略在全球政治经济中都广泛存在。不同国家采取不同战略背后的动机截然不同:一些国家是为了增加其公民的未来收入而在全球经济中寻求利益;一些国家更强调由国家控制其国外资产,寻求在全球经济中打造标杆性企业;还有一些国家利用国家引导的跨国投资接触全球性领先工艺和技术,以使其经济发展模式迈向新阶段。
综上所述,金融化总是与不平等、全球化、资本积累、世界体系等问题交织在一起。但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一是金融化的具体表现发生了变化,国家债务取代了家庭债务的重要地位,并且国家引导下的跨国投资日益普遍。可见,在全球经济低迷不振的背景下,国家被赋予了更为重要的经济功能。二是随着信息技术和数字经济的发展,无形资产对企业日益重要,并在金融化与全球化之外,成为影响企业投资的重要因素。
三、关于资本对分配的影响
国外学者研究资本对分配的影响主要关注两方面:一是对劳资之间分配的影响;二是对富国与穷国之间发展差距的影响。
卡斯滕·科勒、亚历山大·古尚斯基、恩格尔伯特·斯托克哈默:《金融化对工资份额的影响:理论阐述与实证检验》(Karsten Kohler, Alexander Guschanski, and Engelbert Stockhammer, “The Impact of Financialization on the Wage Share: A Theoretical Clarification and Empirical Test”, Cambridge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43, No.4, 2019)
本文分析了金融化与功能性收入分配之间的联系,并对其进行了理论上的阐述和系统性的实证检验。在理论阐述部分,本文分析了金融化影响收入分配的四个渠道,并基于不同的经验方法对其进行了检验。第一,金融全球化导致资本退出的选择增加。第二,在金融化背景下,股东价值导向导致非金融企业的财务支出增加。第三,金融化导致资本市场的竞争加剧,间接地使工人处于不利地位。第四,家庭债务增加导致工人的财务脆弱性加剧,这会削弱其阶级意识。在实证检验部分,本文对14个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1992年至2014年间的面板数据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金融自由化与非金融企业的财务支出对工资份额具有稳健的负面影响。本文发现:金融开放主要影响企业与工人之间的权力平衡;财务成本与资本市场的竞争加剧了食利者与企业之间的冲突,但这一冲突可能通过牺牲工人的利益而得到解决;家庭债务会影响工人阶级的身份认同,破坏工人在劳资冲突中的立场。本文的政策含义在于,工资的停滞是因为资本流动的增加,而不是劳动力流动的增加,去金融化是改善收入分配的一个更为有效的措施。
玛丽亚·N.伊万诺娃:《不平等、金融化与美国经常账户赤字》(Maria N. Ivanova, “Inequality, Financialization, and the US Current Account Deficit”, Industrial and Corporate Change, Vol. 28, No.4, 2019)
美国自1982年以来就持续出现经常账户赤字,且新世纪以来其赤字的增长在加速,并曾在2006年达到美国GDP的6%。与此同时,美国的收入分配与财富分配越来越不平等,且美国经济的金融化不断加深。本文认为,经常账户赤字、不平等与金融化这三种现象的出现并非偶然,它们都是自1980年代以来,美国资本的生产过程通过对外投资和离岸外包进行全球化重构的结果。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资本输出国、最大的国外投资收益接受国和最大的进口国,其进口产品的生产通常有美国资本的参与。这导致美国国内出现了去工业化现象,中等收入、中间阶层的工作大量减少,收入不平等加剧,而美国资本生产过程的跨国化提振了公司利润,从而支撑和加速了美国经济的金融化过程。
因坦·苏万迪、R.贾米尔·乔娜、约翰·贝拉米·福斯特:《全球商品链与新帝国主义》(Intan Suwandi, R. Jamil Jonna and John Bellamy Foster, “Global Commodity Chains and the New Imperialism”, Monthly Review, Vol.70, No.10, 2019)
本文从全球商品链的角度分析指出,南北国家不平等的主要驱动力是现代奴隶工作制度。这是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下中心与外围的精英们强加给南方国家的制度,以此利用劳动价值的商品链来实现全球新殖民主义或帝国主义的延续。研究表明,在21世纪的帝国主义中,跨国公司能够进行不平等的交换,用更少的钱获得更多的劳动力,而这一过程中获得的超额剩余往往被误导性地归功于在中心地区进行的创新、金融和价值提取的经济活动。在一个允许资本国际自由流动、同时严格限制劳动力国际流动的体系作用下,中心经济体与外围经济体之间的单位劳动力成本存在巨大鸿沟,全球北方与南方之间工资的差异大于生产力差异。这一体系压低了外围国家的工资,有可能使南方国家的经济剩余被大量抽走。从本质上讲,商品链中的每一个节点或环节都代表着一个盈利点,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利润率。单位劳动成本最低的国家往往会成为最终生产和组装的地点,也是扩大毛利润率的最关键节点。链条中的每个节点或环节都构成了价值的转移,这在一定程度上被GDP核算的惯例以及计算附加值的方式所掩盖。灵活的全球化生产意味着全球商品链中劳动密集度最高的环节位于全球南方,那里的劳动力后备军更大,单位劳动成本更低,因此剥削率也相应更高。而通过这些商品链,以及它们在低工资国家的关键节点,北方国家的公司能够在更高的劳动力剥削率的基础上,获得对其全球竞争力至关重要的低成本地位。其结果是,跨国公司的利润率大大增加,产生的额外价值往往归功于中心地区的生产,进而导致了中心地区财富的积累。
本杰明·塞尔温、达拉·莱顿:《垄断资本主义时代的世界发展》(Benjamin Selwyn and Dara Leyden, “World Development under Monopoly Capitalism”, Monthly Review, Vol.73, No.6, 2021)
近几十年来,全球化的发展主要表现为全球价值链成为占支配地位的资本主义组织形式。高科技产品、基本消费品、重型资本设备等产品的生产过程分布于许多国家,并由全球价值链进行整合。根据国际劳工组织的数据,在1995-2013年间,参与全球价值链的雇佣劳动者从2.96亿增加至4.53亿。主流经济学忽视了各种对全球价值链的批评。本文利用《2020年世界银行发展报告》的数据说明,全球价值链并没有通过工作的创造、贫困的缓解和经济的增长促进穷国的发展。本文在事实和理论上支持了垄断资本学派的观点,即垄断资本国际化的扩张所造成的结果是剥削程度和垄断程度在世界范围内的加强。
综上所述,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的国内不平等产生机制主要是金融化。国外学者在理论和经验上确认了资本的金融化趋势是影响劳资分配的重要原因之一,直接导致劳动报酬份额的下降。而国际上的不平等产生机制主要是以全球商品链和价值链为具体表现的垄断资本主义体系。这两种机制的共同作用导致财富不断向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少数垄断资本聚集。
四、关于资本垄断与无序扩张
国外学者对近年来垄断程度的新变化以及垄断对整个经济造成的后果进行了研究。同时,他们还分析了资本向自然环境、医疗、教育等领域的扩张。
莱拉·戴维斯、厄兹居尔·奥尔汉甘兹:《美国经济中的竞争与垄断:产业集中度数据说明什么?》(Leila Davis and Özgür Orhangazi, “Competition and Monopoly in the US Economy: What do the Industrial Concentration Data Show?” Competition & Change, Vol.25, No.1, 2021)
本文重点关注了美国非金融企业部门的产业集中度。研究发现:第一,在1997年至2012年间,美国各行业的平均集中度都有所提高,其中,产业集中度的提高主要出现在1990年代末和21世纪初。产业集中度增长的很大部分是由零售和信息服务等行业驱动的。第二,产业集中度、盈利能力与投资之间并没有统一的关系,高度集中的行业并不是利润最高的行业,中等集中的行业赚取的利润率最高。第三,在中低集中度的行业中,企业赚取高额利润,成本加成率较高,这说明,产业集中度不是市场势力的唯一表现,市场份额较小的公司仍然可能拥有市场力量。
托马斯·E.兰伯特:《垄断资本与企业家精神:小企业在衰落吗?》(Thomas E. Lambert, “Monopoly Capital and Entrepreneurship: Whither Small Business?” Cambridge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43, No.6, 2019)
本文关注过去几十年美国经济中企业家精神的衰退及其背后的原因。小企业数量的增加及其创造的工作数量的增长本应是美国经济增长的核心元素。然而,在垄断资本主义之下,经济集中度不断提高,小企业在集中度提高的过程中逐渐衰落,出现了经济停滞的趋势。现有的研究对美国经济中企业家精神衰退的解释包括:其一,美国家庭负债率极高,遏制了创业;其二,面对大企业,小企业的竞争压力更大;其三,在对企业的监管加强的情况下,小企业比大企业面临的困难更多。由于创业需要承担风险,极高的家庭负债率和资金雄厚的大企业都会阻碍创业行为。本文认为,以上这些因素与1970年代以来美国新企业数量增长的放缓高度相关。
约翰·贝拉米·福斯特:《作为一种积累模式的自然:资本主义和地球的金融化》(John Bellamy Foster, “Nature as a Mode of Accumulation: Capitalism and the Financialization of the Earth”, Monthly Review, Vol.73, No.10, 2022)
本文认为,激进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家为保护自然和公共资源免受市场入侵而提出了“自然资本”的概念。近几十年来,新古典经济学把自然资本视为另一种形式的金融化资本。新古典经济学据此认为,解决当前地球生态危机的办法是创造一个市场。同时,所有涉及生态系统的自然过程都被日益视为从属于逐利性的市场交换活动,即使这些活动以保护地球和防止气候剧变为名。这一变化使得资本主义条件下资本的无限积累不断被强化。本文提出,自然资本应该强调实际财富由自然物质的使用价值组成,而不是资本主义经济的商品化交换价值。由于资本主义是一个以指数扩张为目标的积累体系,因此必然会导致自然资源的减少。在世界经济整体金融化的背景下,自然的金融化可能会加剧资本主义经济的波动。最后,本文认为,要放弃“资本的自然化”和“自然的资本化”,承认资本的社会性质及其存在的特定的历史制度。只有以促进真正的、自由的人类发展为目标,才能提供一个克服当前全球危机的途径。
乔尔·莱克钦:《当代资本主义中的制药业》(Joel Lexchin, “The Pharmaceutical Industry in Contemporary Capitalism”, Monthly Review, Vol.69, No.10, 2018)
本文指出,近几十年来,资本主义国家制药行业的盈利能力一直处在行业前列,但实际上,它们的利润并不是来源于药品研发和销售。一方面,制药行业只有约1.3%的税后利润用于新药的研发;另一方面,在制药公司生产和研发的新药中,只有很少一部分药品有助于治疗。本文认为,2010-2015年制药行业发生了严重的亏损危机,反映了在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包括制药行业在内的经济活动重心从生产转向了金融。本文重点分析了资本主义国家制药业的四个特征:第一,制药业为了保持其对金融资本的吸引力,已经逐渐转向了“小众化”模式。第二,在这一模式下,制药企业为了确保正在研发的药物通过监管流程,不得不加强与监管机构和政府的联系与勾结,从而滋生腐败行为。第三,制药企业生存的关键在于有能力延长垄断产品的销售时间。第四,随着价格控制的威胁愈发迫近,增加收入的另一种方式是增加现有和新研发的药品的销量,而实现这一目标的方法则是控制关于如何开药的知识。本文最后指出,制药业的巨额财富及其与监管机构和政府的勾结不断强化其市场势力,商业价值逐步取代公共卫生成为监管机构的优先选项。在此过程中,药物审批环节越来越薄弱,治疗效果越来越差,上市药物相关的安全问题越来越多。增强知识产权保护虽然有利于保护公司利润,但也意味着全球范围内基本药物的获取越来越受限。
塞西莉亚·瑞卡普、雨果·哈拉里-克马德克:《大学对资本积累的直接从属》(Cecilla Rikap and Hugo Harari-Kermadec, “The Direct Subordination of Universities to the Accumulation of Capital”, Capital & Class, Vol.44, No.3, 2020)
本文认为,从历史上看,大学对资本主义的再生产作出了贡献。然而,在历史上,大学被视为脱离市场的一个独立领域,仅仅是资本积累过程的间接参与者。1920年代至1960年代,美国出现了一种线性的创新模式,这一模式分为三个步骤:一是开展基础研究,这是应用研究的来源;二是通过实验性的开发过程,将科学研究与企业联系在一起;三是将成果扩展至整个经济。全世界的一部分资本垄断了对创新进行规划并从创新中获利的能力。个别资本之间在创新能力方面的巨大鸿沟导致那些缺乏创新能力的资本只能处于从属地位,并让渡了一部分剩余。本文认为,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大学直接参与了资本的积累。
综上所述,国外学者的研究揭示出新世纪以来美国等西方国家的资本垄断程度不断加深,阻碍了中小企业的发展,导致经济停滞。与此同时,资本不断将自然资源、药品、教育等关系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本资源商品化、金融化,并从对这些资源的排他性占有中获取垄断利润,这反映出资本无序扩张的严重后果。
作者:齐昊,中国人民大学全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研究员、经济学院副教授;高新远,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硕士研究生;何宁致,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硕士研究生
本文转载自国外理论动态(2022年第3期)。文章经授权发布,如需转载,请统一注明出处人大政治经济学论坛及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