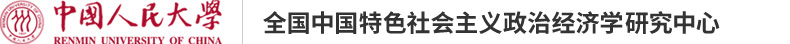卫兴华:关于学好用好政治经济学的一些思考——在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新)成立会议上的讲话
发布时间:2025-09-10编者按:卫兴华教授是“人民教育家”与“最美奋斗者”荣誉称号获得者,是我国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和教育家。为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值此2025年教师节之际,本公众号特推送卫兴华教授在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新)成立大会上的讲话和《大先生——中国教育名师列传》卫兴华教授一集,以致敬大先生,并祝所有教育工作者教师节快乐!
借着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所)成立会议的机会,我想就学好用好政治经济学讲四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人民大学经济学院的过去、现在和未来。题目很大,内容很小。人民大学最初建立经济系,后来改成经济学院。人民大学从1950年起到60年代中期,给全国培养了大量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师资,经济系也给全国高校培养了多批政治经济学教学与研究人才,更早的政治经济学教研室还为全国培养了两届研究生。我于1950年当研究生的时候,就有北大的张友仁与我同班学习,后来有萧灼基等是我系的学生,分配到北大。复旦大学蒋学模也是与我研究生同班。还有一些外校的教授也来学习。经济系还办了多期教师进修班,以提高外校教师的理论水平。一直到1964年,还办了两期《资本论》进修班。后来搞“四清运动”和“文化大革命”就停止了。原来我们系和学院有一大批高水平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教师,不仅有政治经济学的人才,也有西方经济学的人才,比如说高鸿业,他在美国就是专门研究和讲授西方经济学的,回国以后学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他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来驾驭西方经济学,出版了全国通用的西方经济学的教材,说明西方经济学哪些我们可以借鉴,哪些是错误的。可惜他已经走了。吴易风教授既深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又深知西方经济学,但他也年老体衰。人民大学经济学院需要后继有人。
人民大学过去还有多名既熟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又精通经济学说史的人才,如孟氧、李宗正等。现在这些学有专长的老教师大部分去世的去世,退休的退休。人民大学经济学院还继续工作的老教师中我是年龄最大的,94岁了。以宋涛同志为首的早期的一批经济学人才大都走了或退了。所以我在校院领导面前不断讲,我们经济学院要有紧迫感,要有危机感,要看到我们后继乏人,要赶快加强我们的人才队伍建设,要赶快扩充我们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人才队伍。当然,我们对西方经济学也要搞好和加强团队建设。我们怎么样走向未来?我觉得必须赶快培养新的能在经济学领域起领头作用的年轻专业人才。现在我说要有危机感,就是因为除了前述我院后继乏人外,还应看到目前全国重点高校的经济学院都在向经济学的高地不断地攀登,我们应该向人家学习,取长补短。人家好的思路、好的举措,要认真学习。一方面,更要注重培养我们自己的人才,我们优秀的博士生、博士后要留下;另一方面,要引进有真才实学的高水平的人才。
我们经济学院的理论经济学多年来一直被评为第一。其中老本也许有点作用。但我们的老本不多了。怎么样培养新人才,怎么样加强我们的理论经济学团队建设,怎么样加强我院理论经济学教材建设,怎样做大做优做强我们的科研能力和成果,这是我们需要解决的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怎样学好用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习近平同志讲要学好用好政治经济学。首先要学好,才能用好。如果学歪了,就很难用好。有很多马克思主义理论问题,理解错以后,会对我们国家的发展产生重大的负面影响。事例很多,我只举三个例子。
第一例,马克思主义强调社会主义要大力发展生产力,但决定发展生产力的要素是什么?长期以来我国不少政要和理论家浑然不知马克思的论著中一再强调科学在推动生产力发展中的作用。在“文革”后期,竟有掀起批判科学是生产力的怪事。起因是这样的:胡耀邦就职科学院时,搞了一个科学院汇报提纲,其中讲了科学是生产力。邓小平同意科学是生产力,但该提纲没有引证马克思强调科学是生产力的话,被认为是自己编造的。邓小平又被免职后,因他讲过科学也是生产力,《红旗》和《辽宁日报》都发表文章,批判这一观点。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竟被当作反马克思主义批判。追根溯源,之所以会出现否定和批判科学是生产力的怪事,正是因为我们过去对生产力的概念本身就没有搞清楚。长期以来,我们讲生产力二要素,即劳动力和生产工具。后来又讲生产三要素,加入劳动对象。国内学界还进行了二要素、三要素的争论。其实,马克思在其著作里讲了生产力的多要素,特别强调科学是生产力的重要因素。马克思把分工协作、自然力、管理、生产组织等也作为生产力因素,而且马克思明确地讲,随着经济的发展,生产力的因素会更多。我们现在信息技术的发展、人工智能的发展、新的科技创新,都超出了马克思所看到的生产力的诸因素,构成生产力的因素越来越多和越先进了。弄清构成生产力的多因素,才能更好地利用这些因素快速发展生产力。
第二例,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里讲,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有一个过渡时期,等于过大江、大河,乘船过渡,由此岸过渡到彼岸,此岸是资本主义,彼岸是共产主义。马克思把共产主义分成两个阶段——低级阶段和高级阶段。低级阶段就是现在所说的社会主义。原来毛主席也是讲,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建立是一个过渡时期。他讲社会主义建立,没有说社会主义建成——我们到现在也没有建成社会主义,还处在初级阶段。毛泽东主席认为在过渡时期,就是过渡到建立社会主义。后来,我们跟苏联论战,发了九篇批判苏联修正主义的文章。其中有一篇就是关于过渡时期的论战。邓小平在1989年和戈尔巴乔夫会谈的时候说,过去两家讲了很多空话,我觉得是讲了一些错话。我们把整个社会主义社会叫做过渡时期,批判苏联不把社会主义看作是过渡时期,主张过渡时期是过渡到共产主义高级阶段。列宁讲过渡时期不能不是阶级斗争更加残酷和更加尖锐的时期,这样一来,社会主义作为过渡时期就不能不是阶级斗争更加尖锐、更加残酷的时期。但列宁说的是社会主义建立前的过渡时期,而不是整个社会主义。本来,过渡的彼岸是共产主义,而作为共产主义低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就在彼岸的前方,过渡到社会主义就是过渡到彼岸。错解“过渡时期”是服从于“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需要的,导致提出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
第三例,关于资产阶级法权(权利)的问题。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批判《哥达纲领》离开所有制,空谈“公平分配”“平等权利”。即使是搞按劳分配,它的平等权利也只是等量劳动取得等量劳动产品的权利,这个等量劳动相交换,原则上相当于商品等价交换的平等权利,等价交换也是等量劳动交换。而资产阶级承认等价交换,而且能够实行等价交换,所以马克思从按劳分配原理中抽出其中的等量劳动交换,将其视作旧社会的痕迹,是资产阶级法权。我们错误理解了马克思讲资产阶级法权的本意,流行起限制和批判资产阶级法权的论述。“文革”中张春桥在上海发表了一篇批判资产阶级法权的文章,《人民日报》被要求转载。把资产阶级法权错误理解为等级制度。毛主席是一个伟大的政治家、军事家、理论家、文学家,有很多创新的理论,包括新民主主义理论,包括后来鉴于苏联经济发展上的缺失,提出按农轻重顺序安排经济发展等。我们对前人的理论要实事求是地分析,正确的要继承发扬,错误的东西我们也不要回避。毛主席把资产阶级法权看作是等级制度,是儿子对父亲、下级对上级,像老鼠见了猫似的,认为这都是不公平,都是资产阶级法权;认为解放后废除了供给制,实行工资制,工人实行八级工资制,也是资产阶级法权。其实,资产阶级法权是资产阶级宣扬的权利,不管事实如何,资产阶级高喊的是平等自由权利,它反对封建主义的时候,是用平等自由反对封建主义的等级制度,等级制度不是资产阶级所要求的权利。所以我觉得,误解资产阶级法权,给我们带来了经济发展上的一些负面的东西。计件工资取消了,稿费取消了,许多拿工资的人几十年未涨工资。
所以我们学马克思主义,一定要认真地按照其原意把握它,学好才能用好,学不好就会用错,就会对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造成伤害。
第三个问题,是关于社会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问题。这方面有不少模糊不清和误解错解的问题。我们搞理论经济学、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既要对前人的科学理论坚持继承,又要有所发展。应该提出自己独立的新的见解来,要有创新。如果只是重复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重复了其他人的理论观点,没有自己的独立见解,不能提炼出新的观点,那是不完全的。
另外,对于误解错解的各种观点,应澄清理论是非,提出自己的正面见解和对误解错解的辩驳。举个例子。我比较早地在《江西社会科学》1986年第4期上发表了一篇有关改革的文章。经济体制改革开始时是叫做管理体制的改革,我写文章说,经济改革似不应限于管理体制的改革,重要的是要探寻公有制的实现形式,要探寻按劳分配的实现形式。因为我作为一个小小学者,提出这个问题没有人注意到。但是当后来中央文件提出,要探寻公有制的实现形式,提出股份制是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时,掀起了热烈的讨论。但是有一个很大的误解,《经济日报》《光明日报》《北京日报》,都误解了实现形式的提法。怎么误解的?他们说过去我们把全民所有制(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看作是公有制的实现形式,而现在不同了,要把股份制作为公有制的实现形式了。按照他们的意见,现在股份制是公有制的实现形式了,过去的实现形式过时了,也就是要放弃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了。然而,在股份制中,国有资本还是国有的,私人资本还是私人的。他们把公有制的存在形式和实现形式混淆了,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是我国公有制的存在形式,租赁制、承包制、股份制等是其实现形式,二者不能混同起来,我写文章进行了辩驳。
再一个事例是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我考虑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强调的是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相结合,那非公有制经济是不是也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组成部分?我比较早地在几家报刊上提出这样一个观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广义、狭义之分。如果从狭义的角度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相结合。但我考虑市场和市场经济是全国统一的,不能按照不同的经济成分分别建立不同的市场和市场经济。因为我们以公有制为主体,可从广义上构成统一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从资源配置上来讲,不管是私有还是公有,进入市场,对经济都起资源配置的作用。这是我比较早地提出来的观点。就是说明非公有制经济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组成部分。后来,中央文件明确讲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后,我国经济学界,包括一位有影响力、有社会带头作用的老学者,提出了中央文件把非公有制经济也作为社会主义经济,突破了宪法。不少学者附和其观点,而且自称已形成“共识”,使整个理论向负面倾斜了。我在一个刊物上发表了不同意见,我的一位老同学方生同志也是那一派的代表,他出头跟我争论,并从政治取向上批判我,说我的观点是反对市场经济、反对邓小平理论。他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应摒弃传统的社会主义”,实质上是要摒弃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我跟他争论了两年。现在习近平同志已把问题讲清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发展与创新。
第四个问题,是理论界对十九大文件的某些权威性解读并不符合其原意。新时代的社会主要矛盾变化了,主要矛盾成为人们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主流媒体发表了冷溶等众多著名理论家的解读,成为主流观点。出版的导读十九大的文件也采用了冷溶的观点,用区域不平衡、城乡不平衡、收入不平衡、生产力落后,还有原始生产工具等来解释主要矛盾。铺天盖地都是这一个观点。我发表几篇文章,大胆地反驳这个观点。十九大文件没有他们讲的这个观点。我认为,所谓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本意是指,随着我国生产力快速发展,人民收入显著提高,消费需求也随之提高了。需求方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要求有更高质量、更方便、更安全、更科技化、更个性化的消费品。虽然生产与供给的水平也提高了,但低端产品过剩,高端产品还不能充分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因而形成供求双方新的不平衡。解决的途径是提高生产质量和效益,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搞科技创新,建立新的经济体系等。《马克思主义研究》2018年第9期以“本刊特稿”形式,发表了我的论文《应准确解读我国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科学内涵》,是对我的有关观点的支持。
我讲这些问题是想说明,我们的理论工作面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社会主义经济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还有许多复杂的理论是非需要澄清。澄清理论是非,才能有理论创新。需要有大批真学真懂真用的经济学人才。宋涛同志曾对我们讲,要培养经济学的梅兰芳。可惜我们这一代没有出梅兰芳,寄希望于下一代。他们中要有真正大师级的梅兰芳,成为世界著名经济学家,他们在全世界有话语权,其著作在全世界有影响力。萨缪尔森的经济学著作在全世界都有影响力,我们中国哪一个经济学家出的教材在全世界翻译?所以寄希望于我们经济学院将来能培养这样的经济学大家,寄希望于我们的后代。
作者:卫兴华,“人民教育家”国家荣誉称号与“最美奋斗者”荣誉称号获得者,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中国人民大学荣誉一级教授
本文转载自政治经济学评论(2019年第3期)。文章经授权发布,如需转载,请统一注明出处人大政治经济学论坛及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