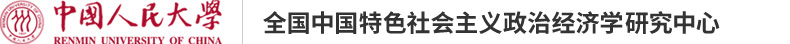林岗:高质量发展与经济增长速度
发布时间:2020-07-08内容摘要:高质量的发展需要物质产品和服务的供给以较高速度的持续增加来支撑。对于未来我国能否保持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本文通过对三个“共识”的批判,得出我国经济仍然具有以较高速度增长的基本条件。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的高质量发展所包含的“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理念的贯彻落实,是能够得到以速度较快的经济增长的坚实支撑的。

尽管高速经济增长不等于高质量发展,但在经济增长过低的条件下,社会发展肯定不可能是高质量的,因为高质量的发展需要物质产品和服务的供给以较高速度的持续增加来支撑。近些年出现的增速下滑,是不利于实现高质量发展要求的,所以党中央提出在坚持高质量发展原则的同时,还要稳增长,即保持经济增长的较高速度。但是,对于未来能否保持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无论是实际经济工作者还是经济学者中,都有不少人持比较悲观的看法。这种看法是以对我国未来经济条件的某些所谓“共识”为根据的。但是,这些“共识”与事实不符,是站不住脚的。
第一个共识是断言在人口增长率下降、劳动年龄人口减少、“人口红利”消失的条件下,经济增速必定以较大幅度下滑。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的持续高增长主要归因于人口因素,是这个共识的另一面。然而,问题是这种增长能在多大程度上归结到人口因素上?实际上,在出生率持续下降(实行计划生育以后人口自然增长率长期在0.4%左右的极低水平上),劳动年龄人口规模增长很慢的情况下,我国的高速经济增长主要不是依靠劳动力投入的增加,而是依靠劳动效率的提升。1991-2010年,我国劳动生产率的年增长率始终高于7%。特别是自2001年以来的大多数年份,其年增长速度都在8%以上,最高甚至达到了14%。为了明确劳动生产率高速增长对经济高速增长的决定性作用,可以比较一下劳动生产率提高和劳动力数量增加对过去20年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在1991-2010年的经济增长过程中,劳动生产率的贡献远高于劳动力。特别是自2006年以来,劳动力增长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低于4%。这使我们想到尼古拉斯·卡尔多和西蒙·库兹涅茨这两位对经济增长理论做出了重大贡献的经济学家。他们在各自总结出的现代经济增长的典型化或特征性的事实中,都将人均产出即劳动生产率的持续提高列在首位。卡尔多对这个事实的表述是,“人均产出持续增长,且并不趋于下降。”库兹涅茨的说法是,“人均产出和人口增长率都高,且人均产出增长率更高。”这当然不是巧合,而是现代经济增长的普遍规律的反映。劳动生产率快速提高对我国过去30多年的经济增长的巨大贡献,是对卡尔多和库兹涅茨所揭示的这个规律的验证。
事实上,改革开放后二三十年我国的经济增长,固然与人口因素有关联,但主要是在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基础上,大量农业劳动者转移到高人均产值即高生产率的工业部门,以及工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在技术进步和经济体制改革推动下快速提高的结果。如果农业劳动者的生产率保持在十分低下的状态,其产出除了养活劳动者本人而所余非常有限,就不会有足够的储蓄用于现代工业部门的投资,劳动人口也就不可能大量转入高生产率的现代工业部门。在这种情况下,为提高总产量而向传统农业领域不断增大劳动力投入,结果只能是边际产量和平均产量的持续下降。与这种下降相伴随的,是经济的缓慢增长以致最终陷入停滞。同样,如果工业生产部门的劳动生产率保持低下状态,经济的快速增长也是不可能的。
第二个共识是认为我国投资率过高,浪费严重,效率低下,并据此主张将投资率降下来,进而断定投资率的大幅下降将不可避免地导致增长速度的下滑。判断我国投资率是否过高,首先要看投资是否超过了储蓄。改革开放以来,在大多数年份,我国的投资率都高于40%。根据2000年以来的历史数据推算,未来我国的总储蓄率虽然会有所降低,但也不会低于40%。这不仅比目前美、德、日等老牌发达国家高出约20多个百分点,而且比韩国这样的新兴发达国家高出十几个百分点。与阿根廷这样的陷入所谓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相比,则要高出1倍。较高的储蓄率,为较高的投资水平提供了基本保障,而较高的投资水平则是经济以较高速度高质量发展的不可或缺的动力之一。显然,从投资与储蓄的关系来看,说我国投资率过高根据不足。
从效率的角度看,投资必须是高效的,浪费是不能允许的。但是,要做出关于投资效率高还是低的正确判断,需要搞清楚我国的投资效率到底是个什么状况。国民经济的宏观投资效率,即固定资本的增加对GDP增长的贡献,可以用资本边际生产率(ICOR)来衡量。根据定义,ICOR越高,单位GDP增加量所需固定资本越多,即投资效率越低。在用ICOR来衡量宏观投资效率时,应当注意产业结构的影响。资本密集产业比重较高的国家,ICOR普遍较高。如果一个国家正处在工业化城市化加速、先进装备制造和其他重化工行业规模扩张、基础设施大量投入的时期,很容易出现ICOR指标提高的情况,但这并不表明投资因不经济的利用而效率下降。从1990年以来,我国的投资效率在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之后,都大幅下滑,这是反危机强刺激措施的结果。如果剔除与两次危机对应的ICOR峰值,在1990-1997年的正常发展时期,ICOR数值8年低于3,而且多数年份低于2;在亚洲金融危机与全球经济危机之间的另一个正常发展时期,即2001-2008年,ICOR数值9年都低于4,其中从投资率跨过40%的2003年到全球经济危机开始的2008年,ICOR数值6年持续低于3。在这两个正常发展时期,随着投资率的提高,ICOR数值有所上升,但幅度不大,并未造成什么严重不利后果。相反,这两个时期都是以较低通胀条件下的高速经济增长为特征的。这两个正常发展时期,也正是我国产业结构快速升级、资本密集行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明显上升、基础设施建设大规模推进的时期。这两个时期之间ICOR数值的有限上升,是经济发展过程中良性结构变化的结果,而不能用投资因不经济的利用而效率下降来解释。
根据世界银行数据库的资料计算,从1981-1990年、1991-2000年、2001-2010年、2011-2013年这四个时段,我国的ICOR分别为2.25、3.05、3.19和4.02,而美国是6.71、5.91、8.85和8.47,日本是7.08、12.88、11.53和14.81,德国是9.071、12.21、12.39、23.82,韩国是3.30、4.69、7.32和10.66。事实上,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投资率在世界上是名列前茅的。较大的投资规模加上投资的较高效率,是改革开放以来推动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力量,也是今后我国经济快速增长的重要保障。我国某些部门和行业目前存在的产能过剩,确实存在去产能的问题。但是,对于目前的产能过剩形成的原因,应当有全面的认识。与这些过剩产能相关的过去的投资决策,是根据当时国内和国际市场的需求状况做出的,就当时的情况而言是合理和必要的,是市场机制发挥决定性作用的结果。也就是说,所谓产能过剩,是相对于现在发生的国内经济结构升级和国际经济的萧条状态而言的过剩,并不是生来就过剩。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尤其是在全球化的市场经济中,商业周期是不可避免的,经济发展经过一段繁荣之后,总是会有产能过剩的问题出现,总会发生范围或大或小的去产能过程,出现过去投资形成的某些固定资产的“湮灭”。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投资应当大幅度减少。相反,要进一步推动技术创新,从而尽快实现供给侧结构调整(这意味着要开辟许多新的投资领域),同时帮助一些仍然具有竞争力的企业渡过难关,避免去产能导致失业过度增加和有用固定资产的不必要毁灭。遏制经济的持续下滑,投资就必须保持足够的力度。
第三个“共识”是认为我国的国际竞争力变弱将导致经济增长率下跌。其理由是我国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长速度逐渐减缓,劳动力成本呈现上升趋势,出口产品的价格优势将丧失。这个理由事实上是不成立的。因为,考察国际竞争力不仅要看一国工资的绝对水平,还要看一国工资在国际上的相对水平,也就是要进行工资水平的国际比较。可以把近20年出口额加起来一直占世界出口总额60%~70%的27个OECD国家2000年之后的平均工资数据,与中国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实际平均工资水平做个比较。2000-2011年的12年,中国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实际工资增长了346%,显著高于27个OECD主要国家的增幅(实际平均工资的增幅位于7%~189%)。但是,截至2011年,中国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实际平均工资水平仍显著低于27个OECD主要国家,仅为美国的12%、日本的10%、韩国的25%。也就是说,虽然中国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实际工资已上涨到了一个较高水平,但与世界主要出口国家比较,我国的廉价劳动力成本优势仍然非常明显,而且这种优势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还会保持下去。
在作为我国潜在竞争对手的部分非OECD国家中,南非、墨西哥等发展中国家目前实际平均工资明显高于我国,但增长速度较低;俄罗斯、乌克兰等国家目前实际平均工资水平略低于我国,但增长速度较高。至于亚洲国家,除了马来西亚外,印度、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泰国、越南的实际平均工资均明显低于我国,其中印度、印度尼西亚、越南的工资水平尤其低。如果仅就实际工资水平而言,这些国家对我国来说是有一定竞争优势的。但是,在比较劳动力成本优势时,不仅要看劳动报酬水平,还要考虑劳动生产率。根据国际劳工组织(ILO)的观点,单位劳动成本(ULC)即平均劳动报酬对劳动生产率的比值,是能够更为精确地反映一个产业或国家的成本优势的指标。2000-2011年的12年,我国的单位劳动成本由0.243增至0.436,年均增长6.7%,其增速与27个OECD主要国家相比属于较低水平,而且就2011年的数据来看,中国单位劳动成本仅仅高于爱沙尼亚,略低于波兰和斯洛伐克两国,较其他发达国家仍有明显差距,仅为美国的58%,日本的40%,韩国的72%。与南非、墨西哥、俄罗斯、巴西4国相比,我国劳动力成本仅高于墨西哥,与其他3个国家存在明显差距,仅相当于南非的30.2%,俄罗斯的91.3%,巴西的55.6%。与工资成本相对低廉的前述亚洲6国相比,我国单位劳动力成本仅略高于马来西亚,而明显低于其他5个国家。当然,从长远看,与这些国家相比,我国可能会失去单位劳动成本的优势。不过,由于这些国家中的多数在基础设施、劳动生产率、资本存量、劳动者受教育年限、科技创新能力、企业管理水平、营商环境和其他社会条件等方面,与我国的较大差距很难在较短时间消除,同时,考虑到我国劳动生产率持续增长的前景,它们提高劳动生产率从而在单位劳动成本方面形成对我国的优势,虽然可以说是一种不能排除的可能性,但无疑是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实现。2014年5月25日,英国《经济学家》杂志发表了一篇题为《中国将保持制造业霸主地位》的文章,得出了与我们的结论类似的看法:“所谓劳动密集型生产商将离开中国寻找廉价目的地的说法,是夸大其词。通过对众多新兴经济体2013-2018年劳动生产率同工资上升的对比预测,我们发现,鲜有(投资)目的地会比中国更具成本竞争力,且没有任何经济体的劳动生产率增幅会超过中国。”近年,即便美国搞贸易摩擦,我国的出口和外国投资仍然保持良好态势,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国的竞争力并未减弱。
此外,还应看到,近20年来我国出口贸易结构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附加值较低的劳动密集型低端制造业产品出口在全部出口中所占的比重下降,而附加值较高的资本密集型高端制造业产品的比重正在逐步提高。1995年我国5类典型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比重达到了37.95%,而典型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比重仅为24.51%。2003年(亚洲金融危机后),5类典型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比重达到了25.68%,而同期典型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比重上升至45.89%,此时我国的国际贸易已告别了“卖数亿件衬衣买一架飞机”的时代。2013年,贸易结构的变化进一步加深,5类典型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比重降至18.80%,而同期典型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比重进一步上升至51.00%。可见,目前我国出口贸易中,典型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成为主要支撑。虽然劳动密集型产品对于我国出口贸易仍然重要,但其比重却大幅下滑,比1995年下降了19.15个百分点。今后,劳动密集型产品在我国出口中所占比重还会下降。因此,从出口结构来看,劳动力成本上升对于我国出口的冲击是比较有限的。这也提醒我们,在国际贸易中,低收入国家与我国并不在同一个竞争层次,一些低端的劳动密集型的产业向低收入国家转移也是正常的,并不会挤占我国出口在世界总出口中所占份额。
从以上对三个所谓“共识”的否定,可以得出我国经济仍然具有以较高速度增长的基本条件。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的高质量发展所包含的“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理念的贯彻落实,是能够得到以速度较快的经济增长的坚实支撑的。最后,还想顺便指出的是,“基数大增长就慢”这个流行看法也是可以商榷的。这个看法在20世纪80年代就提出过,孙冶方先生曾撰文否定了,先生当年的论说当下仍然有启发意义。
本文刊发于经济学动态 (2019年7月)促进高质量发展笔谈。文章经授权发布,转载须注明出处及作者。
(作者:林岗,中国人民大学原副校长,一级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