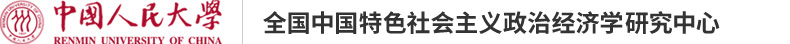谢富胜等:“劳动新形态” 价值创造问题的政治经济学解析
发布时间:2023-10-29内容摘要:WEB2.0时代出现了电商平台开发、网红直播、发帖打榜、游戏陪玩等“劳动新形态”。国外部分学者从受众商品论、数字劳动论、非物质劳动论与情感劳动论等理论出发,认为诸劳动新形态均创造价值,但上述理论或将消费活动与劳动混淆,或将非生产领域劳动与生产领域劳动混淆,从而误判了大多数劳动新形态的价值创造性。基于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分析可知,只有生产使用价值且生产出供交换的产品或服务的劳动才可创造价值。发帖打榜为消费活动,电商平台开发为不生产使用价值的流通领域劳动,均不创造价值;文娱与服务平台的才艺直播、陪玩等劳动新形态通过服务生产出使用价值来换取报酬,因而创造价值。
随着维基(Wiki)、脸书(Facebook)、红迪(Reddit)、推特(Twitter)等互联网公司的兴起,互联网进入了“用户生产内容”(UGC,User Generated Content)的WEB2.0时代,数字平台扭转了互联网的逻辑,通过动员全体用户的力量,在平台上生产出近乎无限的信息资源,大大改善了人们的互联网使用体验。如果说工业革命带给人们“庞大的商品堆积”的现实世界,那么WEB2.0的革命则带给人们“庞大的信息与数据堆积”的虚拟世界。在WEB2.0时代,人们建构并使用各类数字平台的活动被统称为“劳动新形态”,而掌控这些平台的互联网公司绝大部分都是以盈利为目的的平台资本。由此,WEB2.0背景下劳动新形态是否创造价值遂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所谓劳动新形态,从平台、供给方、需求方三类主体的角度来看,可分为建构数字平台的开发活动、充实数字平台的创作、展演与服务活动和使用数字平台的休闲消费活动,如平台开发、网红直播、发帖打榜、开源分享、游戏陪玩等。而要回答这些劳动新形态是否创造价值这一问题,笔者认为必须关注两个方面:第一,活动是否为生产供交换的产品或服务的劳动;第二,在满足条件一的前提下,该项劳动是否属于生产领域的劳动。
一、劳动新形态是否创造价值:来自国外的讨论
针对WEB2.0背景下劳动新形态是否创造价值这一问题,国外学者主要有三种不同看法:一是认为WEB2.0背景下平台资本所获得的价值来源于用户的活动或本公司雇佣程序员的劳动;二是认为绝大部分劳动新形态并不创造价值;三是认为应分别看待不同劳动新形态的价值创造性。
(一)劳动新形态创造价值的理论
第一,受众商品论和数字劳动论。WEB2.0时代来临之前,部分国外学者从理论上分析了大众传媒与后福特生产方式下的价值创造问题,为WEB2.0背景下劳动新形态的研究提供了方法指引。斯迈思的受众商品论认为,大众媒体制作节目免费给受众收看这一行为将受众作为“受众商品”生产出来并出卖给了广告商,受众观看广告的所谓“受众工作”便具有了生产性。贾利(Sut Jhally)和利文特(Bill Livant)则使用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等范畴,论证了受众观看广告的价值创造性。尽管受众商品论是前互联网时代的理论,但它仍不难推导出WEB2.0背景下受众的劳动同样具有价值创造性的观点。
进入WEB2.0时代,大众媒体已不再是协助商品流通的唯一手段,福克斯敏锐地洞察到受众商品论的内核——受众在资本循环中扮演了积极的作用,并以此将当时已经出现的数字劳动这一概念理论化,提出了数字劳动论。他对数字劳动概念做了如下界定:“本书所讨论的劳动形式是所有类型的数字劳动,因为它是数字媒体的生存、使用和应用中所必需的集体劳动力的一部分。”可见,福克斯数字劳动论的重点是社交媒体上的数字劳动,即“产消者”(prosumer)劳动。他认为用户在社交平台上的活动留下了包含个人信息的数据,这些数据随即被平台收集、打包并出售给广告商,平台由此攫取了价值。这样,用户便成了既消费社交平台,又生产数据商品的产消者。福克斯据此讨论了平台开发者劳动的价值创造问题,他指出:“印度软件工程师创造的价值很大程度上并没有留在本国……而是被西方资本挪用和拥有。”也就是说,这类劳动新形态是创造价值的。数字劳动一词最早的使用者特拉诺瓦(Tiziana Terranova)也认为这类带有智力性的数字劳动是创造价值的。还有一些学者也指出软件开发、软件设计等劳动新形态创造价值。
第二,非物质劳动论与情感劳动论。它们主张人类运用智力与情感从事的劳动一般而言都是创造价值的劳动。20世纪90年代,随着意大利制造业从福特制生产方式向后福特制过渡,非物质劳动作为对福特制下重复性体力劳动的替代物逐渐走进了自治主义学者的视野。拉扎拉托(Maurizio Lazzarato)提出了“非物质劳动”概念并将其界定为:“影视制作、广告、时尚、软件制作、摄影和文化活动等。”他认为,非物质劳动正处在生产与消费的交汇点上;非物质劳动通过信息交流,为消费者的需要、想象和品味赋予形式,生产出社会关系的同时创造出使用价值与经济价值。拉扎拉托所强调的非物质劳动,本质上只是一种通过信息传递交流促进商品资本循环的脑力劳动。随后,哈特(Michael Hardt)和奈格里(Antonio Negri)扩展了拉扎拉托的界定,使得非物质劳动论发生了情感转向:“因此,这批作者最严重的缺陷之一就是在处理生命政治社会中的新生产实践时倾向于仅仅触及它在智力和非物质方面的表现。然而,肉体的生产和情感的价值在这个环境中无论如何也是具有核心重要性的。”他们将这种生产肉体与情感价值的劳动称之为“情感劳动”(affective labor),而之所以要强调情感劳动相对于侧重智力的非物质劳动的异质性,是因为情感劳动“超越了计算机所定义的通讯和智能模式”。在情感劳动论看来,常见的情感劳动,诸如在健康产业、娱乐工业以及家庭中所执行的劳动,均创造剩余价值。情感劳动论所强调的在场的、亲身的情感服务本不在劳动新形态的范畴之内,但在WEB2.0背景下,情感劳动借助数字媒介克服了时空的限制,使得传统空间的在场延伸到数字空间的在线,哈特、奈格里等人由此应用情感劳动论来研究WEB2.0背景下劳动新形态的价值创造问题,认为商业资本可以在线上通过情感劳动创造品牌价值,社交媒体上粉丝的情感劳动也可以为节目制作方无偿创造价值,生产性游戏中的公会成员亦能通过玩家之间的情感劳动为游戏公司创造价值。值得注意的是,在情感社会学领域亦存在“情感(绪)劳动”(emotional labor)论,其与自治主义的情感劳动论相比,更侧重劳动者被规训的一面,其源于社会学家霍克希尔德(Arlie Hochschild)对空乘、追债人等低端服务业劳动者的田野研究。该理论认为,劳动者在特定的时刻深层表演出与自身本真情绪相悖的情感,这本身是一种异化的、为资本创造利润的劳动。在WEB2.0的语境下,也有学者应用情感(绪)劳动来研究外卖平台骑手与社交平台女性粉丝的劳动新形态,并认为这些劳动新形态为资本创造了剩余价值。
(二)劳动新形态不创造价值的观点
支持劳动新形态创造价值的学者们正确地看到了WEB2.0背景下劳动新形态促进了平台资本利润的增长,然而却将利润归结于劳动新形态所创造的价值。而认为劳动新形态不创造价值的学者正是看到了这一逻辑漏洞:在社会总资本层面上,利润存在一定意味着剩余价值的存在,但断言某行业的利润源于本行业雇佣工人与用户在内的所有参与者贡献的价值,却不一定是正确的。
有学者认为,WEB2.0背景下网络平台的用户的浏览、观看行为不创造价值,平台资本的剩余价值来源于平台资本家所建构的虚拟文化空间对其他行业的租金汲取。例如,陈(Chin-Hsien Chen)认为,广告商支付给媒体的费用是一种虚拟资本的折现值,受众的注意力则是未来可能会给广告商带来消费现金流的虚拟资本,其本身并没有价值,本质上是一种价值的求偿权。卡拉威(Brett Caraway)指出广告商支付给媒体的费用是一种租金,而非受众所创造的价值。利基(Jakob Rigi)等人亦持此观点,并以统计数字证明了受众的总观看时间不足以解释媒体巨额的收入。尼克松(Brice Nixon)也认为广告商租借了传媒资本家生产的文化空间,受众并不生产价值。斯尔尼赛克(Nick Srnicek)指出,并非所有平台资本都以广告营收作为收入的主要来源,且平台公司并非直接售卖数据给广告商,而是以拍卖广告空间来获取收益。此外,还有学者从多种角度反对WEB2.0背景下劳动新形态创造价值的观点:WEB2.0背景下网络平台的用户并不与平台构成雇佣劳动关系,用户并非工人,故不创造价值;用户观看广告的活动处于流通领域,而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卷研究商业劳动时已经明确流通领域不创造价值;用户的活动不是劳动,不创造价值;数字产品均可零成本复制,其再生产所需的社会必要劳动几乎为零,WEB2.0背景下的劳动新形态不创造价值。
总体来看,持有不创造价值观点的国外学者在批判WEB2.0时代兴起的诸多新理论时,其论据不仅建立在《资本论》第一卷所重点论述的产业资本增殖规律之上,而且将目光进一步放在了《资本论》第二卷所论述的资本流通过程和《资本论》第三卷所论述的商人资本与地租理论之上,较持前一种观点的学者更全面地把握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内涵。然而,一味地否定WEB2.0背景下劳动新形态创造价值这种“一刀切”的姿态也可能走入了误区。在众多劳动新形态中,存在着如才艺表演、网约司机等只是运用数字技术作为辅助,但本质上仍属于传统劳动过程的劳动形态,这些劳动形态的价值创造性仍需进一步考察,不可一概而论。
(三)介于创造与不创造价值之间的观点
关于WEB2.0背景下劳动新形态价值创造这一观点,有学者既没有作出完全肯定,也没有作出完全否定的结论。麦克斯韦(Rick Maxwell)认为,受众商品的价格具有虚拟性,其价值并非来自观众,而是来自文化产品的生产者,如导演、演员、后期制作人员等。这种观点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一方面否定了受众、用户、消费者等群体通过注意力等形式创造价值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则从传统劳动过程的角度肯定了文化生产工人的价值创造性:WEB2.0背景下使用电脑、互联网进行工作的文化生产工人只不过是使用传统纸质媒介写作、策划的工人的新形态而已。阿维德松(Adam Arvidsson)与科莱奥尼(Elanor Colleoni)认为,社交媒体的价值和用户的使用与观看时间毫无关系,这类活动并不创造价值,社交媒体的价值源于平台方或广告商主动创造出能与消费者共鸣的情感环境。安德烈耶维奇(Mark Andrejevic)认为,在UGC平台上,用户自主创造的内容不属于被剥削的范畴,不创造剩余价值,而真正被商品化的则是用户无可避免地被跟踪记录的浏览数据。
上述分析表明,国外学术界对于WEB2.0背景下劳动新形态的价值创造问题尚未形成一致的意见,这种分歧从逻辑上可以被分解成两个问题:(1)受众收看大众媒体,用户使用社交媒体等消费活动是否可以称之为劳动;(2)如果某些WEB2.0背景下的劳动新形态的确可以称之为劳动,这些劳动新形态又是否是创造价值的劳动。如果对两个问题中的任意一个作出否定的回答,就会得出WEB2.0背景下劳动新形态不创造价值的结论。进一步而言,假若大部分劳动新形态都不创造价值,那么平台、媒体等资本的利润来源便只能从价值转移这条理论路径来解释了。
WEB2.0背景下劳动新形态的价值创造问题较早地在国外传播政治经济学等领域得到广泛关注与研究。不过需要明确的是,传播政治经济学实际上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传播学领域中的具体应用,其所提出的一系列理论与观点,应以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为基础。由于WEB2.0背景下劳动新形态仍然属于人类社会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四环节的循环过程,因而讨论其是否创造价值的问题,必须依据马克思关于劳动与价值创造、资本主义生产劳动与价值创造、使用价值与价值创造的分析。
二、何种劳动创造价值:基于经典文本的分析
国外学者在使用受众商品论、数字劳动论、非物质劳动论与情感劳动论研究WEB2.0背景下劳动新形态时,多将其指认为创造价值的劳动。然而,这些学者均缺乏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思想真正全面而又细致的考察。马克思关于劳动创造价值的分析,除三卷《资本论》以外,还见于《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等文本,只有系统地考察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分析的文本,才能确立WEB2.0背景下劳动新形态创造价值问题的理论依据。
(一)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辩证统一的理论视野
WEB2.0背景下劳动新形态本质上仍未脱离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四大领域,正是因为分配、交换、消费这些领域在一定限度内对价值生产起到了促进作用,才会导致国外部分学者将某些处于分配、交换、消费领域的劳动新形态误认为是创造价值的劳动。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以下简称《导言》)中便明确了分配、交换、消费同生产的辩证统一关系。作为核算国民经济价值的方法论基础,谢克(Anwar Shaikh)等将经济活动中生产、分配、社会维持、消费四个部分确定为四大“领域”,与马克思在《导言》中划分生产、分配、交换、消费时所使用的德文词“Sphäre”一致。
马克思首先讨论了生产领域与消费领域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他认为,生产过程本身也是消耗劳动力商品和生产生产资料的过程,“生产行为本身就它的一切要素来说也是消费行为”。这种“生产的消费”并非日常用语中所指称的“原来意义上的消费”,“原来意义上的消费”就是人通过消耗物品或他人的劳动力,完成人自己身体的再生产,这就是“消费的生产”。马克思指出,这种生产“是与原来意义上的生产根本不同的”,“在第一种生产中,生产者物化,在第二种生产中,生产者所创造的物人化”。马克思早在19世纪就批判了将消费与生产混同起来的错误,“对于一个黑格尔主义者来说,把生产和消费等同起来,是最简单不过的事。不仅社会主义美文学家这样做过,而且平庸的经济学家也这样做过”。从辩证法的角度来看,如果取消消费与生产之间的对立性,那么生产这个概念本身就会因为缺乏与其对立的要素而走向消解。在《资本论》中,马克思也强调了消费对于资本周转的两重角色:首先,消费是商品资本流通的必经环节,“商品在流通的前半段同货币换了位置。同时,它的使用形态便离开流通,进入消费。它的位置由它的价值形态或货币化装所占据”。消费者使用自己的收入进行消费,成功将商品资本转化为货币资本,资本由此完成了“惊险的一跃”,利润也从无到有实现了出来,但消费并没有从无到有生产出利润,利润根本上源于剩余劳动。其次,消费活动还对应着劳动力再生产范畴。“实际上,工人的个人消费对他自己来说是非生产的,因为这种消费仅仅是再生产贫困的个人;而对资本家和国家来说是生产的,因为它生产了创造他人财富的力量。”马克思此处虽然将工人的个人消费指认为“生产的”,但如之前强调过的,“生产的”并非是“生产领域的”,并没有创造价值。
分配和交换也辩证统一于生产之中。分配既是生产成果的分配,也是生产条件的分配,虽然离开了分配,生产只不过是一个“空洞的抽象”,但马克思仍然赋予了生产相对于分配的决定性地位,“例如,掠夺一个从事证券投机的民族就不能同掠夺一个游牧民族一样”。正是两个民族的生产方式不同,决定了其分配与再分配方式的不同。而交换作为生产与消费之间的中介要素,同样统一在生产之内,但生产亦起着主导交换的作用。分配与交换领域虽均统一于生产领域之内,但也不可抹杀其与生产领域本身的差异性。促进资本流通、协助生产资料在各个产业资本家之间进行分配的劳动,虽间接地是生产过程的前提条件,但并不因此成为生产价值的劳动。正是因为没有正确理解甚至直接忽视了《导言》的理论意义,许多国外学者并没有考虑WEB2.0背景下劳动新形态所处在的经济领域,致使其落入了两大理论误区:或是直接将消费活动论证为创造价值的劳动,或是将分配、交换等非生产领域内的雇佣劳动论证为创造价值的劳动。
(二)消费活动、劳动与价值创造
对于直接将消费活动论证为创造价值的劳动这一理论误区,可以从三个方面进行说明:一是消费活动不等于劳动;二是消费活动并未有目的地生产供交换的商品或服务;三是消费活动无目的生成的痕迹与数据不能成为认定其创造价值的理由。
第一,消费活动不等于劳动。马克思所分析的劳动,应包含“赋形”和“疲劳”两大内涵。塞耶斯认为,马克思的劳动是一种“赋形过程”, “因此,劳动作为使用价值的创造者,作为有用劳动,是不以一切社会形式为转移的人类生存条件,是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即人类生活得以实现的永恒的自然必然性”,这侧重于主体对客体的作用。如果侧重的是客体对主体的作用,更应该称之为受教育、消费或休闲。譬如歌唱家唱歌,通过控制自己的声带发出声波,赋予了无序自然世界以有序的特征,属于劳动;然而在听众那里,则是声波作用于感官引起主体的反应,属于消费活动。人们观看电视、刷朋友圈,是期望图像景观满足人的欲求,而非想借此改造某物。马克思在《导言》中谈到:“在生产中,人客体化;在消费中,物主体化”,其强调的亦是物对主体的作用。我们不能将所有消耗时间精力的活动都称之为劳动,更不能把原本是消费活动的受众活动、产消者活动称之为劳动。消费总是要花费时间精力的,一切有目的的活动也都是需要一定的执行时间的,不可因为存在时间精力的消耗就将活动指认为劳动。在劳动“赋形过程”的属性之外,马克思还指出了劳动的强迫与疲劳的特征:“因此,工人只有在劳动之外才感到自在,而在劳动中则感到不自在,他在不劳动时觉得舒畅,而在劳动时就觉得不舒畅。因此,他的劳动不是自愿的劳动,而是被迫的强制劳动。”马克思也阐明了劳动与自主活动的区别,并认为共产主义社会应消灭劳动,“而共产主义革命则针对活动迄今具有的性质,消灭劳动”。由此可见,马克思只是将劳动视为人类赋形活动的一个具有历史性的特殊阶段,劳动意味着人身的劳累和产品的被剥夺,而在共产主义社会,这种历史的劳动将会被扬弃。可见,在马克思本人的理论建构中,劳动都意味着不自愿与不自由。而消费活动却是满足主体需求的一种活动,其恢复了体力,放松了身心,不符合上述特征,不能与劳动相混淆。消费活动既然不是劳动,那么自然不创造价值。
第二,只有生产出供交换的产品或服务的劳动才能创造价值,而消费活动并未生产供交换的商品或服务。马克思从异质的使用价值的交换中抽象出价值这一同质的范畴,意味着价值在逻辑上导源于使用价值的可交换性,导源于“为别人生产的使用价值”。而这一“为别人生产的使用价值”背后的同一性则是无差别的人类抽象劳动,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才说“使用价值或财物具有价值,只是因为有抽象人类劳动对象化或物化在里面”。因此,只有生产出供交换的产品或服务的劳动才能创造价值。需要注意的是,这一条件在逻辑上只是必要条件,不满足该条件的劳动必然不创造价值,但满足这一条件的劳动不一定创造价值。如商业工人为商业资本家执行一定服务的同时换取其谋生的产品,但商业工人在纯粹流通领域中的劳动并不创造价值。
第三,无目的活动生产的副产品没有价值,消费活动无目的生成的痕迹与数据不能成为认定其创造价值的理由。一切人类活动,无论是生产还是消费活动都会留下痕迹,一旦被记载在媒介物上,就成了具有相对稳定性的数据。人们消费活动留下的痕迹通过程序员预先编写的算法收集起来,才可形成具有商业性和解析性的有序数据。消费者并不是目的性地留下数据,收集数据的过程中真正目的性的劳动是标注员和程序员的数字劳动:前者有目的地生产出训练算法的数据集,后者有目的地设计具有特异性的程序来收集消费者数据。马克思曾区分过盗窃已伐之木与捡拾枯木的行为,前者属于对经过人类有目的性劳动获取的财产的侵犯,而后者只不过是将已经自然脱落的树枝捡走,这种自然脱落的树枝并不是由目的性的劳动所中介,故而并不是侵犯林主的财产。由此可见,捡拾枯木应只考虑采集者的劳动,而不能认为掉落的枯木本身就具有价值。从目的性角度而言,产消者和自然脱落的树枝的地位是等同的,预测消费者偏好的绝大部分数据根本不可能以资本主义的方式大规模再生产,而只可从用户杂乱无章的行为中捕获。占有数据的平台则仿佛占有了肥沃的土地,可凭借此优势收取级差地租甚至垄断地租。而如果数据的生产是标注员目的性劳动的结果,那么当此种数据应用于生产领域时,其价值将会在一定期限内等量转移到生产出来的产品中,而不会新增价值;如果数据不是标注员劳动的结果,而是监视用户或者大自然(如气象、水文数据)等取得的结果,那么这种源于无目的性活动的数据就不具有价值。
综上,消费活动并不是劳动;消费活动不会产出任何用于交换的结果,其本身并不能被商品化,不创造价值;消费活动留下的痕迹与数据并非消费者有目的地专门生产,只是消费活动的副产品,因此消费活动并不创造价值。
(三)生产劳动、生产领域劳动与价值创造
既然不生产用于交换的产品的劳动以及无目的性的活动不创造价值,那么生产用于交换的产品的劳动或具有目的性的劳动创不创造价值呢?马克思在一系列文本中分析了生产劳动与价值创造的关系,生产领域劳动与价值创造的关系。这些文本表明,商业、金融等领域部分雇佣劳动属于生产劳动,但生产劳动不一定创造价值,只有生产领域劳动,即创造使用价值的劳动才可创造价值。相应地,非生产领域的生产劳动劳动也不创造价值。
首先,生产劳动不一定是创造价值的劳动。马克思指出,判定劳动是否是生产劳动,不在于其自然形态如何,而在于其能否为他的雇主带来剩余价值。“只有直接在生产过程中为了资本的价值增殖而消费的劳动才是生产劳动。”需要注意的是,无论是在《1861—1863经济学手稿》还是在《直接生产过程的结果》中,马克思谈及的生产劳动都仅仅是在直接生产领域内谈论问题:“我们在这里研究的还只是生产资本,就是说,还只是用于直接生产过程中的资本。后面我们还要谈到流通过程中的资本。” “至于资本的其他职能怎样——以及资本在这些职能中使用的代理者怎样——只能在以后加以阐述。”以上文本说明,在劳动属于生产领域的前提下,如果劳动力是被资本主义地雇佣的,那么他的劳动就是生产劳动,如果是与收入相交换的,那么就是非生产劳动。劳动是不是属于生产领域更多地取决于劳动的自然形式,劳动是不是生产劳动则更多地取决于其社会关系,同一劳动既可以是生产劳动,也可以是非生产劳动,这是雇佣关系变化导致的结果。在《资本论》第二卷中,马克思指出商业劳动既不生产价值,也不生产剩余价值;在第三卷中,马克思却又指出商业劳动对商业资本来说是生产劳动。故而,生产劳动并不等于创造价值的劳动,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的唯一目的就是自身的增殖,一切可以为资本带来更大货币量的劳动对资本而言就是生产劳动。在现代社会中,大部分经济活动都以企业的形式组织起来,以盈利为主要目的,所以大部分劳动都成了生产劳动。然而诸如商业、金融等部门的劳动都是不创造价值的劳动,国外部分学者将非生产领域内的生产劳动误认为是创造价值的劳动,混淆了生产劳动与创造价值的劳动这两个不同的概念。
其次,只有生产领域内的劳动才是创造价值的劳动。谢克认为,一种劳动只有处在生产领域内,才是一般意义上的生产性劳动,才可生产使用价值。在马克思的文本中,对各类具体劳动形式进行分析时才指出这类劳动是否创造价值、创造的是价值还是使用价值的问题:
第一,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将价值与使用价值相关联起来。第一卷开篇一节题名即为“商品的两个因素:使用价值和价值(价值实体,价值量)”,在这一节末尾,马克思也谈到“如果物没有用,那么其中包含的劳动也就没有用,不能算作劳动,因此不形成价值”。那么,使用价值具有怎样的特点呢?“物的有用性使物成为使用价值”,这句话容易使学者落入只有物质产品才具有使用价值的陷阱,从而将一些消费性服务或非物质商品拒斥于使用价值的大门外。马克思在《1861—1863经济学手稿》中明确指出商品的物体实在性和创造价值无关,“但是,对劳动的物化等等,不应当像亚·斯密那样按苏格兰的方式去理解……这种存在形式和商品的物体实在性毫无关系”;马克思明确指出服务具有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对于提供这些服务的生产者来说,服务就是商品。服务有一定的使用价值(想像的或现实的)和一定的交换价值”。
第二,《资本论》第二卷对商业劳动的研究认为,生产或增加使用价值的劳动才可创造价值。马克思之所以将纯粹流通的劳动界定为不创造价值,是因为它们没有生产、改变使用价值。他之所以将运输劳动界定为创造价值,是因为它们改变了商品的位置这一物理属性。无论是客运还是货运,都是物质生产部门,因为货运改变的是普通商品的位置属性,客运则改变的是劳动力商品的位置属性。“商业使产品获得新的使用价值(这一点一直到零售商人都适用,他们秤、量、包装,从而使产品获得适于消费的形式),这种新的使用价值花费劳动时间,因而同时是交换价值。”可见,只有创造新的使用价值的劳动,哪怕是称量、分包产品这类在商业中执行的劳动,都是创造价值的。
第三,重商主义和古典政治经济学认为价值的多少和财富多寡有关,而使用价值恰好也有财富之意。无论是重商主义还是古典政治经济学,其研究价值创造和生产劳动是为了增大社会财富,促进经济繁荣。这种观念也潜移默化地进入到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之中,马克思提到:“当然,如果这一部分大得不成比例地再生产出来……那么财富的发展自然会受到阻碍。”说明这类“非再生产性物品”生产的无限扩张会影响工人消费资料的生产,长远来看会对财富的发展造成破坏性影响。斯尔尼赛克反证道,如果数字劳动创造价值,那么世界经济应已经步入了一个稳定的增长期。财富的最终目的是消费,消费的特点之一是使用价值的消耗。高峰认为真实财富是能进入个人消费或生产消费的使用价值,这其中又包含商品和供消费的服务,只有真实财富才是价值的承担者。在使用政治经济学的价值概念时,要铭记价值背后的社会经济关系,但也不应忘记其表征财富增长的底色。
上述分析表明,劳动是否创造价值,不应只考虑劳动是否为生产劳动,是否为资本带来了利润,而更应该考虑劳动的直接产物是否具有使用价值,是否处于生产领域,其劳动成果是否促进了全社会可消费产品与劳务的增加。纯粹商业劳动的直接产物是商品所有权的变更,这并非改造自然来获得产品,而是指社会关系的变更。对于整个社会而言,所有权转移前后产品总量不变,所有权的转移并没有创造使用价值。再如马克思提到的簿记劳动,会计在账本上加工,其劳动虽产生了物质效果,但并没有产生更多使用价值,所以马克思将会计及其事务所的维持费用划入了不创造价值的纯粹流通费用之中。会计的劳动只不过是记载代表着商业关系的信息,正如马克思所言:“相反,商品价值的计算,记载这一过程的簿记,买卖交易,却不会在商品价值借以存在的使用价值上发生作用。”不创造价值的工人,其工资品不过是社会总产品的扣除,而这种非生产领域劳动者对生产的促进作用,最终也必须落实到资本周转速度的提高,落实到生产领域工人的有效劳动时间增加与劳动强度增大之上。而真正处在生产领域的劳动,“它为消费提供材料、对象”。由此可见,生产领域劳动就是产出使用价值的劳动。若是该使用价值以商品形式出售换取货币资本或个体户自身的维生收入,则这类劳动便成了创造价值的劳动。
某类劳动是否创造价值,要基于劳动是否处于与流通、社会维持相对的生产领域,那么当工人修建作为商场的房屋时创不创造价值?马克思以固定资本的关系性来说明这个问题:“同一物品可以时而成为生产资本的组成部分,时而属于直接的消费基金。例如,一所房子,用作劳动场所,是生产资本的固定组成部分,用作住宅,就根本不是资本的形式,而只是一所住宅。”马克思在这里区分了固定资本的两种用途:生产资本或消费基金,而用作商场的建筑正是作为非生产费用的基金被消费掉了,工人即使生产了流通场所,仍然创造价值,其根本原因是建筑具有关系性,可以随时被生产地使用。
三、对劳动新形态是否创造价值的具体分析
判断任一活动是否创造价值,首先要分析它是否是劳动,其次要考察劳动是否直接生产了使用价值,最后还要明确劳动者是否为了生产供交换的商品或服务而劳动。只有生产了使用价值,且为了生产供交换的商品或服务的劳动才创造价值。那么,WEB2.0背景下的劳动新形态创造价值吗?
(一)WEB2.0背景下的消费活动不创造价值
WEB2.0背景下传统文化娱乐消费活动的时空可得性进一步扩大,消费者可以随时随地拿出移动终端收看节目、玩电子游戏。UGC平台的出现进一步激发了消费者的主体性,消费者可以在平台上创作属于自己的内容或者与其他消费者共同建设符合自己意愿的网络生态环境,消费者俨然以生产者的形象出现在学者面前。斯迈思的受众商品论、福克斯的产消者理论、自治主义者的非物质劳动论和情感劳动论正是据此将消费者的活动指认为创造价值的劳动,但基于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分析,消费活动并不创造价值。
第一,受众商品论中,受众观看广告的活动不创造价值。首先,观看广告的活动并没有生产供交换的产品或服务,在广告行业,基于收视率、粉丝量等客观指标的定价并不直接支付给每一个收看广告的观众,故而观众的观看活动并没有直接进入商品流通之中。其次,观看广告的活动不是劳动,斯迈思的受众商品论将受众的观看指认为一种工作(work),其虽未使用劳动(labor)一词,但无论工作还是劳动,都应具有塞耶斯所言“赋形过程”的属性。斯迈思认为,受众观看广告,其结果是为自己生产出品牌偏好信息并为广告商生产出从商品资本过渡到货币资本的潜能。这两类结果都不是对物质世界的改造,反过来更像是物质世界对受众主观思维的改造,是物的主体化,符合马克思所论及的消费活动的特点。受众商品论视角下的观看活动,并不创造价值。
第二,数字劳动论中,关于社交媒体上产消者通过浏览、发帖产出数据痕迹的活动不创造价值。福克斯的产消者数字劳动,其行动上表现为使用社交媒体接收并生产内容,如果是纯粹使用社交媒体接收信息,同理应属于消费活动而不属于劳动。如果是使用社交媒体进行发帖,虽在一定程度上是赋形的过程,但因发帖活动出于用户自愿,且活动成果无偿共享于平台上,用户并不认为这是一种令人疲惫的劳动,反而会获得分享的愉悦感,故而也不能认为是一种劳动。浏览信息的平台用户虽留下了浏览痕迹,但这种痕迹毋宁说是直接由收集数据的算法整理而来,对于数据工业的劳动过程分析不应锚定在用户处,而应锚定在技术或非技术工人如何生产出收集数据的算法之上。如果认为数据是一种商品,那么,这种商品并非由用户生产,而是由设计算法的工人所生产。从活动目的不是为了交换而言,用户的活动不创造价值。
第三,非物质劳动论中,在开源平台进行代码共享的活动不创造价值。高技能用户在平台上无偿分享自己的代码与文章虽有可能产出了使用价值,但并未商品化。知识精英无偿地分享自己的创作成果,这种活动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语言来说属于“自主活动”,在生产出对象化产品的同时,主体获得了精神上的满足,物由此复归于主体。在使主体产生满足这一意义上,这种自我实现的活动可以视为一种广义的消费活动,这意味着部分非物质劳动因其使主体获得满足的特点并不能被视作纯粹的劳动。开源分享的活动与产消者活动的共同点在于公开且无偿地分享自己的想法,不同点在于前者较后者而言往往需要投入更多的时间与精力,具有更高的使用价值,但这一不同点仍不构成开源分享活动创造价值的决定性理由。
(二)WEB2.0背景下非生产领域的劳动不创造价值
WEB2.0时代除了用户的网络消费活动之外,还存在着网络服务建构、数字内容专业化生产和借助网络平台进行销售、服务等劳动新形态。网络服务建构主要指受资本雇佣的程序员、架构师等高技能劳动者从事程序编写、网站搭建等事务的劳动,也包括低技能标注员为训练AI所付出的劳动;数字内容专业化生产是指受雇于传媒资本,全职从事文化产品生产的劳动,如视频剪辑、直播才艺表演等;借助网络平台进行销售或提供服务的劳动有如淘宝店家、滴滴司机的劳动。这类劳动显然不属于消费活动,但它们都是非生产领域的劳动,因而仍不是创造价值的劳动。
第一,数字劳动论与非物质劳动论中,诸如开发电商平台的雇佣劳动、专业制作数字广告的劳动,只要不是生产领域内的劳动,就不创造价值。程序是一种抽象的逻辑结构,其本质是控制计算机或其他机器运转的指令规则,在物理空间中体现在存储于硬盘上的一行行控制电路通断的指令。编写程序实际上就是设计和制造机器,如果将程序员类比于机器制造工人,那么似乎程序员的劳动就完全属于生产领域了。然而,并非所有程序都服务于生产部门,诸如商品推荐、偏好选择等程序只是为了促进商品流通等非生产目的。所以,诸如程序员、网站搭建员之类的数字劳动者若是在生产领域劳动,则创造价值。但若是在流通领域、社会维持领域劳动的数字劳动者则不创造价值。以编写淘宝手机应用为例,电商平台提供发现(即商品的自动推广)和搜索(消费者主动搜索商品)等功能,其类似于一个在实体店内富有经验的推销员和匹配员,在客户不明确自身偏好的时候做适当引导,在客户偏好鲜明时推荐相应的产品。而程序员就是销售员的岗前培训老师,教给销售员匹配顾客需求的技能。程序员所执行的,虽不直接是推销,但其仍是附属于流通领域的劳动。电商平台是实体店商业工人在WEB2.0时代的代替,故开发电商平台的劳动并不创造价值。电商平台这一劳动成果,并不能严格地称之为使用价值,之所以人们会产生其具有使用价值的错觉,是因为电商已不是纯粹的商品流通平台,平台中活跃的商家和用户亦提供了部分娱乐功能,但这一平台仍主要是一个商品流通的平台。福克斯数字劳动论与拉扎拉托非物质劳动论中有关程序设计劳动的探讨没有注意到并非所有程序员都服务于生产领域这一问题。同样,为流通领域进行网站搭建、AI训练的程序员和标注员的劳动属于非生产领域,也不是创造价值的劳动。只有开发生产性程序的程序员才是创造价值的脑力工人。对于专业化的数字内容生产者而言,若是生产广告,则属于流通领域,不创造价值;若是生产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化产品,则属于生产领域,创造价值。
第二,情感(绪)劳动论视角下的交往性服务劳动,应结合具体领域进行分析。已有文献指出,发达国家交往性服务业的经理人认识到了情感(绪)服务人员人格化的外表和社交技能对剩余价值实现的促进作用。为了提供稳定且高质量的情感(绪)服务,经理人首先会在应聘者中严格筛选外貌条件、举止谈吐等因素,其次通过培训将雇员主体的人格化技能引导入情感(绪)劳动之中,并对劳动者提供服务的方式方法进行控制。劳动者的人格化技能由此被物化在经理人所制定的工作细则之中,人格化的服务以条文的形式变为了不创造价值的资本,这类交往性情感(绪)服务逐渐也成了标准化的产品。在WEB2.0时代,无论是签约主播、陪玩人员还是线下服务的网约车司机,都必须遵守平台规定的服务规则,其劳动所需技能也会逐渐下降,乃至退化为单位时间内价值创造较少的简单体力劳动。然而,如果认为WEB2.0背景下情感(绪)劳动者的价值创造能力一致趋于退化,那么如何解释达人主播、金牌陪玩等劳动者为资本带来的利润远高于普通情感(绪)劳动者呢?一方面,通过使用化妆品、图像视频编辑等工具,美丽外表、温润声音等人格化技能得以规则地再生产出来,所谓“网红脸”便是指代这一现象。在一些只提供陪聊的服务平台上,其背后的劳动者甚至可以只是经过了培训的、使用变音器的男性。另一方面,通过大规模地买热搜、雇水军、发广告等非生产途径,亦能得以让某一名幸运的情感(绪)劳动者一炮而红。由此可见,达人主播的高收入背后,只不过是资本化的美学、温情与数字技术交互作用的结果。平台借助整饰外表、声音等特质的服装、化妆与数字技术,让从事主播类情感(绪)劳动的外在条件门槛愈发降低,大大简化了情感(绪)劳动者的劳动过程,其天赋特质所带来的创造价值的能力逐渐被资本所占用。由此可见,达人主播所获取的收入仅有少部分是其去技能化劳动所创造价值的实现,大部分则是消费者持有的、以收入为形式的价值之转移,而之所以能形成价值转移,则是因为资本进行了海量广告宣发等非生产性投入。如果达人主播本身就服务于带货行业而不创造文化产品,则其劳动就属于流通领域,完全不创造价值,其获取的收入完全源于价值的转移。此外,消费领域也存在情感(绪)劳动,如粉丝为明星发帖打榜的劳动,其同样是基于自主与自愿,并未生产商品,资本的循环流动并没有直接在粉丝这一层面上进行,而是在传媒资本与经纪公司的层面上运作。一些访谈指出,饭圈女孩将高强度打榜看成“自愿加入的工作”,偶像成功出道后“感觉很开心,所做的都是值得的”。这固然可以视为情感(绪)劳动,但因其不满足劳动的强迫性与疲劳性,这并不是马克思意义下的劳动,因而不创造价值。
值得指出的是,虽然众多WEB2.0背景下的劳动新形态并不创造价值,但非生产部门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促进资本流通、畅通经济循环、提高生产部门企业的利润率。马克思以商人资本为例,“但既然它有助于流通时间的缩短,它就能间接地有助于产业资本家所生产的剩余价值的增加。既然它有助于市场的扩大,并对资本之间的分工起中介作用,因而使资本能够按更大的规模来经营,它的职能也就提高产业资本的生产效率和促进产业资本的积累。既然它缩短流通时间,它也就提高剩余价值对预付资本的比率,也就提高利润率。既然它把资本的一个较小部分作为货币资本束缚在流通领域中,它就增大了直接用于生产的那部分资本。”流通费用作为一种“生产上的非生产费用”,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促进了我国实体经济的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促进数字技术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不断做强做优做大我国数字经济”,我们要把握好数字经济中创造价值与不创造价值的辩证关系:对于不创造价值的部分,应在合理的限度内引导其发展,将消极的因素抑制在一定的范围内;对创造价值的部分,应大力协助其做优做大做强,并以此带动不创造价值的部分协同均衡发展。
余论
WEB2.0时代产生了诸多劳动新形态,国外学者提出众多理论与观点探讨了其价值创造问题,然而这些理论与观点因缺乏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全面考察而与经典的劳动创造价值理论存在矛盾。分析表明,只有在生产领域生产供交换的产品或服务的劳动,才是创造价值的劳动。在流通领域和社会维持领域执行的劳动,本质上是为了创造和维护一种法权或社会关系,其劳动虽有可能形成物质产品或痕迹,却并没有创造价值。
随着物联网、区块链、元宇宙等新技术的发展,WEB2.0时代出现了向WEB3.0时代过渡的趋势。WEB3.0的内涵经过了多重演变,较早的文献将其描述为以物联网技术为辅助的万物互联的网络。自区块链技术发展成熟后,WEB3.0的内涵发生了变化,最新的文献将其概括为一种以去中心化、加密化的区块链技术为基本的实现方法,以反抗WEB2.0背景下网络平台对数据垄断性霸权为目的的新兴网络生态。相比于WEB2.0,WEB3.0将在维护区块链分布式账本、订立智能合约和维护加密通证(Token)系统这三大方面吸纳更多的活劳动,这些去中心化的技术应用有利于进一步明晰产权与契约关系,提高经济活动的透明度和可信度,本质上起到的是产权再分配或经济活动监管的作用。从本文分析来看,WEB3.0下的劳动新形态还是处于分配与流通的非生产领域内,并不创造价值。当下的WEB3.0实践中,因其非生产属性引致的金融化风险格外突出,一些主流的区块链加密货币目前仍被当作金融投机的工具买卖,造成了价格的剧烈波动,在元宇宙中,非同质代币(NFT)因其极端的稀缺性更助长了这类金融投机行为,导致实体经济中大量的价值以租金的形式被汲取。WEB3.0仍在蓬勃发展之中,未来可能会涌现出更多上述形态以外的劳动新形态,其价值创造性仍是一个开放性的问题,有待学者们的进一步观察与研究。
作者:谢富胜,中国人民大学全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总编辑,教授;邓可为,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硕士研究生
本文转载自南京大学学报(2023年第3期)。文章经授权发布,如需转载,请统一注明出处人大政治经济学论坛及作者